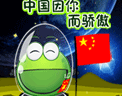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再思录》出版于1995年7月,收集了巴金《随想录》以后近十年间的作品,许多篇章是在病魔缠身时写就的,
文字朴素,内容精炼,风格沉郁。它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随想录》之后,巴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然而许多研究者谈论巴金
晚年思想的时候,往往把这部书排除在外。固然,《再思录》没有《随想录》影响那么大,篇幅那么多,而对问题的思考也不
似《随想录》那么集中和系统,但闪烁于其中的思想火花却仍然清晰可见,而且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在执笔极为困难的情况
下还一字一句地写作,他所要表达的至少对他个
人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这其实是蕴涵着生命能量的“生命之书”。
《随想录》受瞩目,《再思录》受冷落,这个现象本身便显示了这两本书的差别。《随想录》是70年代末和80年
代前期的作品,那是一个群情激昂的共名时代,《随想录》也是一部与社会思潮紧密呼应的书,小到一部电影(《望乡》)一
出戏(《假如我是真的》)的讨论,大到对“文革”的反思和民主化的呼吁,许多社会焦点问题在《随想录》中都有直接或间
接的反应。巴金以个人的方式参与到对社会主题的讨论之中,《随想录》的写作是一种开放式的写作,作者的思想与外在的社
会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双向式的交流的关系,他的立场、观点都是由某些社会事件所触发的,包括在写作过程中,巴金所遭受
的种种批评和不同意见,都曾是《随想录》写作的驱动力。巴金的个人意识在从五四继承而来的社会使命感的承载之下奋勇前
进。而《再思录》则出版于一个思想多元的无名时代,一方面整个社会难以形成一个众人关注的思想主题,另一方面,巴金开
始逐渐从社会退回到个人、自我和内心之中,《再思录》的写作是在相对“封闭”条件下的内心独语,这种转变与巴金的身体
状况相关,年老多病使他不可能迅速地对外在的社会信息进行及时的反应;其次与他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有关,那就是他晚年
主持出版了自己的26卷本的全集和10卷本的译文全集两大作品集:这种工作带动着他回到往昔的时光中,沉浸在青年时代
的人和事的回忆里,使他一度被扭曲的自我,得以有机会与生机勃勃的青春时代重新连通,使得他终于可以以自己的本来面目
面对世人。在那些怀人的篇什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金思想自由流动的痕迹,他终于可以不必太多顾忌外在的各种看法,而进入
了内心的自我表达中,他思考的许多问题已经由具体的人和事而归于抽象:如生命的意义、爱与恨等等,虽然这些文字是那么
简短,可是跃动在文字背后的那颗火热的心和不屈的灵魂却再次伸张出来。所以,将《再思录》与《随想录》这两部书放在一
起,不仅能够看出巴金晚年思想的连续性,而且它们之间许多互补之处恰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更丰富和完整的巴金。
在写作《随想录》的前期,巴金一直在苦苦思索自己是怎么变成“非人”的,而到后期他终于发现了这是敬神灭己的
恶果,而在《再思录》里,他终于旗帜鲜明地喊出了“没有神”,这不仅是对于“敬神”的全盘否定,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坚定
的价值标准在里面,那就是“大家都是人。”巴金在晚年是用自己血泪的经验在捍卫自己在五四的时候所追求的价值标准,“
大家都是人”,就不分等级,就一律平等,同时也都有作为人的人格尊严。
从今天来看,我看巴金提出的话题完全没有终结,“文革”所造成的“精神奴役创伤”还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
那些放弃人格尊严、不能捍卫人格尊严的事情仍旧屡见不鲜。《没有神》是一篇旗帜鲜明的宣言:“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
家都是人。”“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这种呼声似乎发出的很容易,特别是在一个远离了政治
高压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平常,但是背景调换了,实质的内容则未必变化了,比如错当当年的“神”是政治,而今换为
“金钱”的话,马上很多人就能感觉到这个话语中的分量,那些拜倒在金钱脚下,为了金钱出卖人格丧失尊严的事情并没有绝
迹吧?另外,“神”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又有多少人在不同的时代中参与制造那些不同的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理解巴
金为什么要揪着“文革”不放了。有许多问题,巴金可能没有做出回答,但他以他痛切的经验提出了它。
更重要的是巴金还觉得“文革”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比如,在1994年,他谈到书信时,直接的反应是想到60
年代私人通信的内容居然成为相互揭发的罪证,甚至会搞得通信人家破人亡。巴金在《〈巴金书信集〉序》中曾说:“私人信
件可以随意公开,断章取义,任意定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我学习过多次,也发表过不少批判
谬论,但是我至今还不明白一些文人写给朋友的信件会变成‘毒品’,流着一滴滴的血,残害人的生命。”在《关于〈全集·
书信编〉》中,他也提到过书信成为“罪证”的事情。在常人的眼里,这些事情都属于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年代结束了,事
情也就随之而去,但巴金却看到了这种思维方式甚至某些做法在人身上所残留下来的余毒。他讲到在“文革”被彻底否定后,
有人曾经写信提醒他:“当心某某人,他揭发了你。”“揭发”,这个似乎只有“文革”中才经常使用的词汇,在今天依旧潜
伏在我们的生活中,“文革”也并非早已结束的噩梦啊!巴金对此事的反应是:“我感谢这位朋友,但是我也原谅另一个友人
。我常常想:‘责任在谁?’”这声追问,依我看是对那些以为太阳一出,地球上就不再有阴暗的角落的“乐观主义”一个非
常重要的提醒。
如果说在《随想录》中,巴金是通过对大量的社会问题的发言,树立起一个忧国忧民、痛苦坦诚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话
,那么在《再思录》中,巴金是直接地面对自我,面对所走过的道路,在带着深情的回忆中,他对自己早年的思想信仰和自己
的人格的发展有了清醒的认定。巴金已经完全排除了那些顾忌,开始运行在自己的话语系统中了,这里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对
自己信仰问题的再认识。在《随想录》中,谈到这些问题,他总以一种社会公众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思想,现在老人越来越
回到了自己的话语表达系统。《再思录》以沉郁的文字风格塑造了一个孤独的老人的形象——长期身受疾病折磨,语言表达困
难,有话不能倾吐,困郁于心的痛苦和希求得到人理解的痛苦的自我形象。(周立民)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手机上新浪随时了解神六进展 短信看世界与航天员一起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