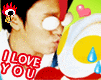| 爵士:在上海华丽转身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19日12:13 新民周刊 | |||||||||
|
撰稿/李宗陶(记者) 蓝调女王诺拉·琼斯(Norah Jones)的“Come away with me”总在上海的空气里飘荡。她似乎总在勾引这座城市的记忆:无论是摩登的过去还是时尚的现在,爵士与上海,都有着最完美的默契。5月2日-5月6日,这座性感的城市将迎来第一个属于爵士的节日。筹备达一年之久的“2004 Jazzy Shanghai上海国际爵士周”邀请了来自挪威、法国、英国、美国
爵士(Jazz),一个乐种在一座城市的70年,竟是如此风情万种,仿佛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徐徐转身,华丽又优雅。 一段“不准确”的记忆 ——从百乐门到和平饭店 77岁的吕天龙在城隍庙他租的“场子”里跟记者讲话,嗓门好大,因为他的耳朵已经不大灵了。“饭可以不吃,爵士不可不听”,从4月1日起,10多个70岁以上、像他一样痴迷爵士乐的老先生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要打造一支城隍庙的老年爵士乐队,“不输给和平饭店的”。吕天龙觉得,和平饭店并不能代表本地老年爵士乐手的最高水平,“高水平的都流散在民间,缺少组织”,他因此觉得可惜。 这个下午,吕天龙给东方票务打了电话,他想听爵士周里两个小号手的演奏,一个是来自挪威的尼尔斯·皮特·穆瓦(Nils Petter Movaer),另一个是来自法国的艾瑞克·屈法兹(Erik Truffaz)。 吕天龙在和平饭店吹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小号,南楼北楼的两个爵士吧他都去演奏过。当年的六人组合中还有两位仍在“和平”,其余的,有的回家听老唱片去了,有的还像吕天龙一样“小打小闹”。 吕天龙不是老克勒,他不叼烟斗,也不用“斯狄克”(stick,拐杖)。他跟爵士乐的亲近解释了为什么在上海,许多上了年纪的、并没有一个资本家父亲的草根会喜欢上这样一件舶来品。他在孤儿院长大,教会背景的教育让他接触到西方音乐,青少年时期参加乐队,正是“百乐门”、“仙乐斯”夜夜笙歌、爵士乐妖娆的光景。 在吕天龙的记忆里,爵士乐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城市并非上海,而是汉口,但1932年落成的百乐门舞厅诞生了中国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杰米·金乐队。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人,如张爱玲所说,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加上一个西方人,“百乐门”的华人爵士乐队亦是华洋交媾的产物。杰米·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他的外国名字如同今天写字楼里的一抓一把的Tony和Maggi,只是个洋标签。 就形式而言,百乐门爵士与美国新奥尔良爵士都是由钢琴、单簧管、萨克斯、小号、长号、低音提琴、鼓、沙槌、打击乐组成,但实质上,它们只是舞曲。 沪上爵士歌手田果安告诉记者,当时的上海爵士乐是由一些喜欢玩的外国水手带进来的。他们做一些掺杂了爵士元素的音乐,在舞厅里流传,上海人叫他们“洋琴鬼”。与由黑人布鲁斯和欧洲音乐交融而生的真正的爵士乐相比,这些音乐并不准确。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上海对一切外来的美妙事物吸纳与兼容。 领班杰米·金大胆地将中国民歌中的一些元素引入了百乐门爵士乐。在此,陈歌辛的作曲功不可没,虽然他本没想到自己的创作会跟爵士产生联系。《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香格里拉》、《夜来香》,串起一代歌后:“豆沙喉”白光,风情万种的李丽华,11岁那年从三千应考者中脱颖而出的韩菁菁(学者梁实秋晚年的妻子)。与周璇的莺转燕语相比,这些同样穿旗袍的女子,在爵士乐的伴奏下,登时洋气而性感起来。 那时候的爵士乐手,带有很强的谋生色彩。跟许多行当一样,许多人有拜师学艺的经历,师傅教会几支曲子,带进场子实习,练熟之后开始跑场子,鲜有变化。本质上,他们跟“镪菜刀磨剪子”或者剃头师傅没什么区别。 吕天龙记得,解放以后,老百乐门更名为红都影院,不再演奏爵士,而“文革”一开始,和平饭店的爵士乐队也解散了。 1980年,和平饭店恢复成立老年爵士乐队。20多年来,上至各国政要,下至黎民百姓,都觉此乃沪上一道风景。乐队也因此多次应邀出访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深受海内外宾客的赞誉。1996年,这个老年爵士吧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世界最佳酒吧之一。’2003莫文蔚上海演唱会,她特意与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合作演绎怀旧金曲,歌名就叫《上海滩》。 英国BBC广播电台的一群编辑也曾慕名前往老年爵士吧,但听完之后,他们私下里对圈内人说,这些音乐与他们浸淫已久的爵士是两回事。圈内人只能解释说,从60年代到80年代,爵士乐与中国人已经相隔太久了。 一座城市总是需要记忆的,而记忆总是需要若干标签的。从“百乐门”到“和平饭店”,从杰米·金到吕天龙,直到年已古稀的郑德仁、王邦声与年轻爵士乐手共同录制的《BMG上海老百乐门爵士五重奏专辑》,它们和他们的存在让人们不至于忘却这里的摩登和繁华,这便是价值。更何况,浮华背后,流动着人类共通的对音乐的热爱,于是准确与否,便不再重要了。 华丽转身——从COTTON到JZ 爵士真正作为一种文化进入中国,是在80年代。那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年代,年轻人拼命收集他们视野范围里所有可能得到的音乐资料:磁带、书籍,还有听电台广播。歌者田果安、话剧演员林栋甫、乐评人孙孟晋都有这样的记忆。 1957年出生的田果安,履历与同时代许多人一样芜杂而不成系统。如果不算拉小提琴、打拳、在家里缝纫一条漂亮裤子、洗印黑白照片之类的业余爱好,他当过车工、描图员、翻译。电大英语专业给了他漂亮的发音,这也是许多听过他歌唱的美国人深感不解的地方:一个能够这样唱爵士的歌手,竟然从没去过美国? 时代断层造就的爆发力往往是惊人的。就像许多知青闻鸡起舞、发愤苦读考上大学一样,田果安养成了经年累月、彻夜不眠地听音乐的习惯。他的听觉如此敏锐,以至于曾在半夜的弄堂里用一个扫堂腿将试图欺侮女子的小流氓扳倒,并因此得到过30元的见义勇为者奖金。 改革开放之初,他在珠海的高级酒店当驻场歌手,拿着让上海人想都不敢想的薪水。当北京唱片店里的英文歌曲磁带还无人问津的时候,他已是专唱爵士的流浪歌手,尽管只“北漂”了半年。“那时的北京人还不像今天这样把爵士乐奉为至尊——比上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顶多是有人将爵士乐与1949年以前的上海流行音乐混为一谈。” 爵士乐从来没能被适当地定义——“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这样回答一位女名流:“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爵士乐,那你永远不会了解它是什么。”“今晚睡不着”、老放一段蓝调的林栋甫回答如出一辙:“爵士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说的。”台湾著名爵士乐评人傅庆堂的解说是:“它不只是概念上的形体,它需要亲身经历才能体会。” 田果安用了近20年时间亲历了爵士。从衡山路的福炉(Full House)酒吧、东湖路7号大公馆、淮海路一代音乐餐厅,直到汾阳路的JZ酒吧,在每一次的摇摆(Swing)和即兴(Play By Ear)中,他体会了“孤独的快乐”和“只属于自己的悲伤”。 田果安这样解读上海与爵士乐的关系:上海这座城,时髦、多元,各种文化在这里都有存在可能;而爵士,是现代流行音乐的“根”。当爵士贴着“小资”的标签进入当代人的视线,并伴随一种高档消费固定下来,听者便从各自的角度赋予爵士乐多种诠释:怀旧、优雅、自由,或者类似靡烂,并从中引申各自的生活理想和情调。“小资”也许可以伪装,但耳朵不可能是虚伪的。音乐的妙处在于它能带来多层次的满足和想象,不仅是学习爵士乐的人连许多摇滚乐手也流露出对爵士乐的迷恋。田果安的发现是:大量音乐都与爵士有关,包括摇滚、百老汇歌舞,以及电影音乐。 2001年,田果安在尔冬强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格什温之夜”的爵士歌曲演唱会。格什温(George Gershwin1898-1937,美国),有史以来唯一一位以爵士音乐和流行音乐作曲家身份而登上古典音乐殿堂顶峰的大师,极有可能是田果安心中的一盏灯。这一天,田果安从头至尾唱了五六十首歌——从下午排练开始,一直到半夜在福炉的日常演出结束。据说,他会唱的英文歌有2000首。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副台长、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陈接章是电台流行音乐发展的见证人。在他看来,伴随着上海20多年来的华丽转身,爵士乐无论怎样茁壮成长都不过分。他说,北京已经搞过2-3届爵士周,但效果并不理想,北京同行曾经对他说:“最适合做爵士的地方是上海。” 乐评人孙孟晋认为爵士乐需要土壤,而上海,恰恰有适宜的土壤。上海有摩登风尚的传统;上海有许多外国乐手,有数量庞大的外国听众,有众多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艺术分子;上海有音乐学院这座摇篮,还有一群分布在各个年龄层的音乐爱好者;上海人讲究生活情调,对时髦的东西学得飞快…… 从淮海中路的COTTON(棉花俱乐部)、茂名南路的JAZZ AND BLUES、四季酒店37楼的爵士37、外滩中心的CJW、希尔顿和波特曼的大堂,还有去年冬天刚刚开业的club JZ,业余的、专业的爵士爱好者都可以找到满足耳朵的去处。其中,club JZ尤其受到圈内人士喜爱,许多赶完场子的爵士乐手常在此地汇合。凌晨时分,当夜与Jazz一起性感起来,台下常常有观众走上台,即兴演奏一段。沪上唱爵士的Jingle、张乐和Coco,也以各自的鬼魅声线让夜晚暗哑,或者摇曳生姿。 现在进行时 ——从新爵士到电子音乐 此番爵士周为爵士迷们打开的,是北欧风情的新爵士之门。 什么是新爵士?爵士周总策划姜亦明说,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当代正在发生的爵士。一个世纪以来,爵士音乐早已突破了传统,融合了电音、民族、摇滚、新古典等各种音乐元素,或优雅或酷眩。而北欧新爵士在近20年里异军突起,引领了全球聆听时尚,这是上海首届爵士周定位于此的原因。 挪威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John Hutchinson回忆说,一年以前,有位年轻的女士(姜亦明)来到领事馆,建议将北欧新爵士介绍到上海,她是如此真诚,所以有了2004年春天的这个爵士盛筵。他说,挪威乐手中有的去过香港,有的去过北京,但都是第一次来上海。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东方演艺公司副总经理徐勇告诉记者,爵士周的运作进行了整整一年,将这些北欧的顶尖爵士乐手一齐请来,追求的是聚集效应,也希望他们与国内乐队(来自北京的刘元四重奏和来自上海的CY/B6)碰撞而擦出火花。当然,“他们都将坐头等舱来上海”。 据说,这些新爵士乐手的出场费加起来,远远超过请一个诺拉·琼斯(Norah Jones)。姜亦明说,明年的上海爵士周,爵士迷有望一睹这位获2003年格莱美奖8项大奖的蓝调女王的风采。 此次上海爵士周,两位本地的年轻电脑音乐高手应邀暖场,1980年出生的CY和1981年出生的B6。 CY,本名丁大闻,2003年毕业于上海大学计算机系。B6,本名楼南令,现在上海某媒体做设计。1999年,CY与Idiot组成双人噪音团体,2000年开始创作电脑音乐,并与B6、susuxx、zoojoo组成实验电子组合I.S.M.U,完成首张专辑《7.9》。2002年11月,CY与B6组成ambient乐队Dustbox(尘匣),这是国内目前风头最健的电子乐组合。他们的作品在美国All music Guide权威网站和英国《The Wire》杂志均获好评。 CY和B6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他们的起步也是从传统爵士开始的。B6从高三时开始玩乐队,担任吉他手,后来做IDM一类的实验电子音乐。他最喜欢的爵士乐手包括John Coltrane、Miles Davis和Herbie Hancock,最初的听觉记忆来自电台节目“蓝调之夜”。而CY对传统爵士始终持有一份敬意和关注,他说上海有许多有意思的爵士艺人,譬如老歌手田果安就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波特曼酒店的音乐总监美国人Danny Woody是一个出色的爵士鼓手,而外滩中心CJW的爵士乐队,是上海最有活力的一支。 他们有时候会去club JZ、CJW、波特曼酒店去听现场爵士乐,M ON THE BUND的国外爵士乐队演出也会吸引他们。“现场的感觉要比一个人在家里听好多了,爵士乐是很直接,当你与那些乐手面对面的时候,你更能感受到他们想通过音乐所传达的情绪。”CY说。 CY说,想要听音乐在上海并不是件难事。他们有比较专一的购买唱片的地方,像曲阜路、新乐路、汾阳路上几家小店。他们依然注重厂牌,像ECM、Blue Note和Jazzland。而电音爵士的风靡,意味着这些电音高手们“哪怕不出家门,也能通过网络找到你喜欢的音乐”。 孙孟晋说,随着时代的迅速变化,打开爵士之门,会注意到它已和迪厅人群搅和在一起,电音编配司空见惯,全球电子的弥漫早已是新人类的标记。这个时代让人无法拒绝身体与电子共震,它在惊涛High浪中把生存的表象抹得一干二净。 与此同时,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影响了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他对爵士乐的深刻理解带动了读者,有一类听众正在成长和壮大。活跃的互联网表明,这一群体的年龄有越来越小的趋势,也就是说,有更多的青年在听爵士乐。他们对音乐的态度更敏锐、更细腻、更专注、更人文,也更能享受。也许这中间仍有人跟风和作态,但从整体上看,他们将是最真诚的聆听者,未来也许会成为爵士乐听众的主流。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