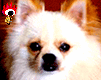魏尔兰的一条命和兰波的两条命(上篇)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5日09:54 新民周刊 | ||||||||||||
|
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魏尔兰和兰波 兰波这个人,我一直是不想碰的。围绕他的传说太多,后来简直就像神话一样,成了一代代诗人的精神支柱。而且一 传十十传百,反反复复那几件事。早熟,有诗才,性格乖
倒是魏尔兰这个人常被拉入兰波的生活,而在这个传奇中他始终是个配角。从某种角度看,兰波这样的人,生活中恐 怕难有除他自己之外的别的主角。倒不是他的诗别人都难以企及,而是他独断的个性。有一些人生来就是杀手,像大树一样, 枝叶越浓密,在其树阴下的花儿草儿便只有死的份儿。而这样的人,往往是人群欢呼的对象。古往今来,这是个永远记取不了 的教训。 话说回来,我后来仔细研究了这两个难兄难弟,发觉两人中,真正具有诗人天命的是魏尔兰,而非兰波。诗歌于兰波 只是青春期的躁动加流星般的天才闪现。二十岁后罢笔,并非天才对命运的精心导演,而是体内已没有这样的需要。他由激情 很快滑向某种清醒,而清醒是诗意的杀手。兰波恰恰是个过于清醒的人,他控制他人和自己的本领都非比常人。他的神话并不 起始于他十五岁开始写诗,而是他二十岁后彻底地离开文坛。所有异常闪亮、又突然中止的东西,都能激起人们无限的想象。 与他相比,诗歌于魏尔兰就是其整个生命,不是疯子难成真正的诗人,用在他身上正合适。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随心灵律动 的人和随利益漂浮的人,魏尔兰属前者中的极至。这种人扑向幸福或灾难都怀着同样的热诚和天真,坏了别人的事却永远以为 自己才是受害者。 但不管怎么说,两人的命运已在传说中被凝固在一起,后世只掌握一点史料的我们,作他想的余地不大。我挑来拣去 ,在两人交往的这场戏里,有几幕简直鬼斧神工。绝大多数人在人生舞台上只是看客,跳出来做戏子的本领和胆量都不够大。 跳出来的人才是传奇,因为他们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我们舒舒服服呆在常规的世界里,他们却从常规的世界进入了非 常规的世界。大作家没有不是混蛋的,也就是无毒不丈夫的意思吧。这样说很吓人,虽没有资格连自己也骂进去,但至少骂倒 了一大片。有什么办法呢,幸福的人生好像是不值得书写的,我们往往只能在悲惨的人生中嗅到那么点永恒的味儿来。 舒瓦瑟尔过道 从地铁十四号线金字塔站上来,向北走一小段磨坊街,就与小田园街交会,过了街就有一个商业长廊舒瓦瑟尔过道。 这类过道在塞纳河右岸歌剧院和王宫花园一带还有好几条,很有旧巴黎的味道。其实就是细长的商业街,只不过上面有玻璃顶 棚避风遮雨。20世纪后半叶大型超市和商业中心出现后,没有人再到这里购买生活必需品,这类过道的保留更多的是旅游明 信片的性质,而没有多少实用性了。不是旅游季节,这里很安静,满可以依稀拂掠几缕旧时代残留的金边。 我那天走进舒瓦瑟尔过道,这类长廊建筑大同小异,因此极容易张冠李戴。那时候我正在大作家塞林纳的生活旋涡里 打转,知道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个过道里他母亲开的花边铺子中度过的。记得他说,母亲一辈子做花边,自己却从没有 用过,因为脑袋里从来就有一条界线,那是夫人小姐用的。这段话我印象很深。老实人常在头脑里划出一些界线,痛苦也好, 幸福也好,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接受这些界线。这种认命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强大基石,那金字塔尖下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一 个命运的叹息,无以数计。有时候我想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监狱。 塞林纳在花边铺子里写作业的时候,已是20世纪初了。19世纪后半叶,这个过道里也发生过一件事,初看是一件 小事,都不值得一提。谁也无法预料起始的那点毫厘会在日后扩展到什么程度。后来超出上述“界线”的那些事,就是从这个 过道开始的。那时过道里还没有塞林纳和他的母亲,里面有一位出版商叫勒梅尔。时值1871年7月,镇压巴黎公社的“血 腥五月”刚刚过去。勒梅尔收到躲到外省去的诗人保罗·魏尔兰的信,问他诗集《好歌》的销售,并且想让他再出一本《失败 者》。那时候所谓出版诗集,印个一百本了不得,名声多在圈子里。诗人靠稿费根本活不下去。 勒梅尔回信说:至少要等一年,让风声过去,才能再出版他的东西。勒梅尔在信尾以一条金规奉劝他:“从你的生命 中去掉两样东西:政治和妒忌,你就会成为完美的男人。” 政治,魏尔兰是不敢沾了,否则要掉脑袋的。巴黎公社期间,他因为政治倾向类同,也因为判断错误,没有跟市府的 人去凡尔赛,而是留在巴黎市政府继续做他的公务员。他没有酒壮胆,其实胆子很小,并不敢参与什么大事。为在新婚不到一 年的妻子面前逞强,参加了国民自卫队,但一天仗都没打。可留下来本身就是“站错了队”。五月流血周一过,他把租的房子 退了,带着已有身孕的妻子,跑到外省暂避。7月中,他被新政府解除了公务员的职务。 8月初回到巴黎的他,对失业倒也并不伤心,本来小公务员的职位就与他命里要做的诗人格格不入,只是安家立命的 权宜之计,靠着祖上的一点积蓄,他做个专职诗人也不错。 这天,他走进舒瓦瑟尔过道找勒梅尔取代收的邮件。信函中有一封吸引了他的目光:信寄自北方阿登省的夏尔城。 是他的旧相识布列塔尼神父寄来的,主要是向他推荐另一个人,夏尔城的一个中学生,十七岁,名叫阿瑟·兰波。这 个陌生青年的信也随信一并寄来。魏尔兰拆信一看,满纸绝望。兰波说,在这个北方阴郁的小城,没有人理解他这个诗人。诗 也随信附了几首。一读之下,果然有才。 几天以后,第二封夏尔城的来信寄到勒梅尔处。比第一封更绝望。随信又是三首长诗。魏尔兰耐不住了,把这些诗拿 给帕那斯派的诗友们看。帕那斯派这个名称来自勒梅尔1866年到1876年间陆续出版的三卷诗集《新诗选》。里面收录 了从波德莱尔到马拉美、魏尔兰等一批新诗人的作品,这批人以古希腊传说中的帕那斯山人自居,主要是反以雨果为代表的浪 漫主义,他们追求诗句的完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帕那斯诗人们读了兰波的诗,被里面交糅的美与狂暴所镇慑。喜欢的人甚至说:“这是新的波德莱尔,更野性。让他 来吧!” 魏尔兰给兰波回了第一封信,信中说:“你有点变兽妄想狂的味道。”“变兽妄想狂”是个精神病学名词,患者精神 错位,想象自己变成了一只狼。又说:“你在诗人这个战场上已经神奇地具备了武装。” 接下来便是为兰波找住处。他逃难回来自己没有再租房子,暂住岳父母处。他费了半天口舌,总算让岳母答应收留兰 波几天。一切准备就绪,他向夏尔城发出了邀请信:“快点来吧,亲爱的知己,我们渴望你,我们等着你。”随信寄去了他在 诗友中为兰波筹集的旅费。 两人谁也没有想到,此番相会具有流星相撞的效果。这一年魏尔兰二十七岁。 尼科莱街14号 尼科莱街在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东面的半山坡上。这条街一百三十年后的今天几乎没大改变。巴黎有时是令人吃惊 的,来到蒙马特高地前的巴尔贝斯区域,我那天一时之间以为到了索马里首都,全是黑人,而且多半是不友善的,穷人难得雅 兴,算是一种解释。走了两条街,顺坡拐进尼科莱街,喧闹便全落下去了。巴黎人怀念的旧世界的影子,幽灵一样徘徊在这样 的小街里,像夹在历史书里的旧书签一样浪漫。走到坡上,有一个小院子,铁栅门后的两层小楼,算是魏尔兰的故居。门口有 市政府竖的铜牌为证。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瞥见了那个“耀眼而悦人的白色身影”——十六岁的玛蒂尔德。几乎是在结婚整整 一年后,他又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兰波。 魏尔兰后来在诗集《不久与往日》中一首名为《爱上了魔鬼》的诗中写道: “他出现在一天晚上,那是去年冬天,在巴黎,没有人知道,这孩子从哪里来。” 其实不是冬天,而是1871年9月10日左右。他们约好在巴黎东站见,那时叫斯特拉斯堡火车站。魏尔兰和朋友 夏尔·克罗去接他,站台上找来找去没见到,双方谁也没见过谁。何况兰波下车见不到人,掉头就走,他可没耐心等人。对什 么事情都缺乏耐心,是他的特点之一。以今天的心理病学分析,可以初步诊断为忧郁症的一种表现。诗意一点说,他是个风一 样不可捕捉的人,停不住的。他自己从车站走到了尼科莱街14号,魏尔兰的岳父母家。几乎跟他同岁而且行将临盆的玛蒂尔 德接待了他。 魏尔兰没有接到他,在酒馆里喝了几杯才回来。兰波已经坐在客厅里。魏尔兰完全没想到那些激烈而无情的诗句出自 这个乡下大男孩的头脑。身体长得太快,皱巴巴的衣服全都吊在身上,一头栗色头发怒发冲冠地竖着,眼睛淡蓝色的,有一股 慑人的光。说话急促而不连贯,总像在赌气,腼腆,动不动脸红,像一只到哪里都嫌空间太小的野狗,在人群中不知所措。他 随身没有带一件行李。 魏尔兰后来对他有这样一段描述,足见最初那致命的吸引力:“那双淡蓝色无情的眼睛里,暗暗含笑地闪烁着一丝温 柔,带着苦怨皱折的突出的嘴唇上,是神秘和性感,而且是怎样的神秘和性感啊!” 晚饭桌上,兰波几乎没有话,三口两口吃完,先自睡觉去了。 与魏尔兰的促膝谈心是在第二天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才开始的。魏尔兰带着客人满巴黎游逛。乡下男孩几乎厌恶一切常 规,他说巴黎公社太手软,凯旋门、巴黎圣母院通通都该炸掉。“罗伯斯皮尔以后发生的事都不重要了。”说到诗人,他也有 一套非同于常的看法,他认为诗人是通灵者、盗火者。花草韵律这些东西,算不上诗,要到事物的尽头去寻找未知物,哪怕这 种寻找令人作呕。兰波很聪明,或者就是少年张狂,他知道不走极端,难出头,舞文弄墨的人太多。就像一百年后的美女作家 们深知“不脱衣服”难以出头一样,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在这个文人正在凝缩成一张画面的时代,若不如此,我们自己的故事 已经没有人要读了。 魏尔兰全听进去了。他的个性与兰波正相反,他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写诗就像他每天吃饭、睡觉一样,是在身体里的 。除了寻求快乐和写诗之外,他像浮萍一样,遇土随土长,遇水顺水流,遇到女人爱女人,遇到男人爱男人。任何一个强人到 他身边,无不被激起统治欲,而他愿意把脖子上的链条交到任何一个他喜欢的主子手里。那么与兰波的相遇正好各得其所。他 在这个少年的愤怒中,看到了一个变兽妄想狂,一个“被流放的天使”,一个想摧毁这个世界而实际上正在被这个世界碾压的 不适应者。而他自己曾几何时,以为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一个体面的婚姻,可以让自己转变为一个适应者。事实上,婚后他 一首诗也没写出来。他从来没有勇气挑战命运,他就像他诗里的“那片落叶”,被“恶风卷裹,随处飘落”(注:引自他的《 秋歌》)。在这个少年激昂的意志下,他又产生了他一生脱不去的那种永远的错觉,我发觉这种永远的错觉是他一生诗歌创作 的源泉。他好像一生就在等着这一刻,他从岸上走下来,“我的灵魂正在向海滩驶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从岸上走下来 的时刻。 而兰波也在等着这一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他,没有一个人愿意从温暖的茧壳里走出来。“在这场野 蛮的滑稽表演中只有我一人握有钥匙。”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分享他这把钥匙的人。兰波一生要寻找的东西实际上不是诗, 而是自由,当他发现金钱是自由的某种保障时,他就弃诗经商了。“我极其固执地要去膜拜自由之自由。”这是他的话。 圣·塞夫兰街 在巴黎,找到圣米歇尔广场那眼喷泉,离圣·塞夫兰街就不远了。从广场过马路到圣米歇尔大街的另一边,就是这条 小街。拉丁区最热闹的一个街区。无论白天晚上,游客不断。希腊烤肉店和土耳其羊肉夹馍店一家接一家,还有中餐馆,原来 中餐馆不出来拉客,现在学希腊人,站在门口叫客。真是好的不学!不过这个旧时代穷文人和艺术家聚居的街区,除了要从旅 行者口袋里掏钱,早已没有了往昔的灵魂。晚上要过了十点进去,游客走了一半,黑夜掩去了不好看的,留下暖暖的灯光,一 点点东方的色彩、气味和声音,才给你旧日在这种小街上一天天积攒下来的幻觉。就这么一点点,转瞬即逝。 魏尔兰潦倒后住过这条街,9号门口现在是一家沙瓦奶酪涮锅店。我下面要说的这一幕与这个9号尚没什么关系。魏 尔兰还远没有到潦倒之日,虽然已丢了工作,但多少还有个家,过着小资产阶级温饱有余的生活。 在尼科莱街14号,两个诗人一日比一日迟归。何况乡下男孩的无礼也到了被下逐客令的时候。魏尔兰只好又去找朋 友克罗收留兰波。然而没有几天,兰波撕了克罗珍藏的书作草纸,克罗异常愤怒,兰波因此不告而别。魏尔兰满城去找,踪影 全无。这个头发里藏满蚤子的男孩跑回老家了?据说这满头蚤子是他的秘密武器,碰到不喜欢的人,神父之类,他头发一甩, 溅人家一身。不过这都是后来传说的佐料,真实程度有多少,已经无人追究。 魏尔兰正绝望,一天,就在圣·塞夫兰街,他一眼看见兰波。男孩身上又脏又破,人瘦了,原来他跑掉后,与流浪汉 为伍,靠翻垃圾寻找食物。魏尔兰心酸了,他觉得自己对他有责任。他把他带进餐馆,让他饱餐一顿,保证从此再也不抛弃他 。 保证容易,负担这个不愿找工作干的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兰波当时有一套理论,诗人是不干活糊口的,做诗人就 要承受牺牲。这未尝不是真理,只不过这个牺牲别人也得分摊。据后来玛蒂尔德说,魏尔兰在六个星期里花掉了两千多法郎。 这可是个大数目,他做公务员时一年的工资也就是这个数。魏尔兰找到了兰波,又去求朋友捐款,他筹到一笔钱,保证每天至 少有三个法郎让兰波吃饭。当时的一个成功者、文名不下雨果的大诗人泰奥多尔·德·邦维尔愿意把佣人住的一间小阁楼捐出 来让兰波住。一帮文人们称这野小子为“缪斯的婴儿”,就是人人都要给他一口奶。到了12月,魏尔兰的积蓄像雪一样融化 了。他开始卖自己收藏的书,又向老母亲借钱。而兰波并不为别人的慷慨所感动,靠施舍度日,让他更愤世嫉俗。在邦维尔提 供的小阁楼里住了没几天,左邻右舍就不满了。结果他又得挪地方。 兰波很快就对这帮他曾远远仰慕的文人产生厌恶,接触任何事必定失望是他的宿命,逃都逃不掉。而文人在人群中虽 不是最卑鄙的但却是最懦弱的。兰波恰恰最不能原谅这一点。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国家,都有其文人圈子,像一个小社会一样 互相依存。被网罗其中的人,有大鱼,但多数是小鱼。所以圈子都是为小鱼而设的。据说魏尔兰的一帮文友请他去咖啡馆,他 给请他的人一个背影,除了张嘴向地上吐痰,嘴唇动都不愿动。要不干脆往长椅上一躺睡大觉。邦维尔请他到家里谈诗,说他 的《醉舟》该怎么写,兰波出来时,嘴里骂了一句:“老蠢货!”有意思得很,这些后来全成了传奇必要的原料,被解释为天 才对庸才的挑战。只不过当时受伤害的并不止受他无礼的人,他自己也成了受害者。巴黎文化圈对他最初的欣赏和同情很快变 成了排斥。连魏尔兰也被拖进去,因为人家认为他保护一个根本不值得保护的人。兰波周围已是一片真空,唯有魏尔兰越陷越 深。已经没有人愿意为兰波提供住处了,魏尔兰只得自己掏钱为兰波租房子住。 10月份,魏尔兰做了爸爸,但一个婴孩的降生已改变不了什么。诗人的情感是无疆界的,所以他的家里人未必能改 变什么。何况在兰波眼里,做父亲无疑是向世俗让了一大步,诗人活着的理由是创作,而不是传种接代。魏尔兰把时间都奉献 给了兰波,玛蒂尔德几乎看不到他,而且回来也是喝得酩酊大醉。魏尔兰贪杯是有名的,但在遇到兰波之前,他还有顾忌。在 兰波的鼓动下,两人一起到酒精世界里寻找事物尽头的未知物。兰波做这些事是清醒的,魏尔兰就不同了。他一喝多,马上变 了一个人,从温柔的兔子可以变成暴烈的老虎。回到家,玛蒂尔德一表示不满,魏尔兰就“炸”。动手的事也就时有发生,第 二天酒醒后,必是痛哭流涕下跪求饶。魏尔兰一直存有幻想,以为常规世界可以永远忍受他的荒唐,他并没有兰波那样的决绝 ,兰波在这个世界不想那个世界,到了那个世界就永远关上这个世界的大门。魏尔兰却一心想脚踏两个世界。殊不知两个世界 之间从来就没有桥梁,必须有所选择。 玛蒂尔德以向法院提出身体与财产分离,向魏尔兰发出了警告。当时法律还没有离婚这一条。魏尔兰慌了手脚,他有 了新的统治者,却并不想放弃旧的统治者。玛蒂尔德提出的和好条件就是一条,与兰波分手,而且兰波必须离开巴黎。魏尔兰 去求兰波,让兰波为挽救他的婚姻暂离巴黎。被兰波大大地嘲笑了一番。哪有为一个“蠢女人”剥夺他自由的道理? 在魏尔兰的恳求下,兰波最后勉强让步,但他绝不回老家夏尔城,而是由魏尔兰出钱,让他在北方小城阿拉斯暂住, 等待魏尔兰稳住玛蒂尔德再说。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