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上海都市村庄:家庭主要收入靠打工(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15日14:26 新民周刊 | |||||||||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户口”在上海已成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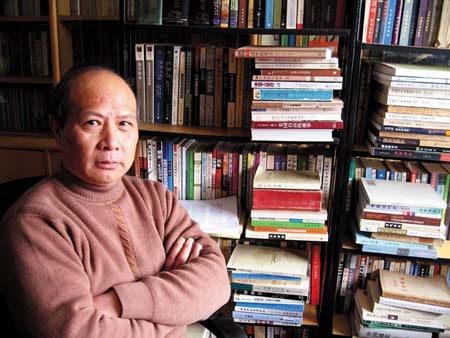 曹锦清:新农村是让农民有安全后方  嘉定乡镇农民春节时领取镇保养老金和医疗金  农妇荡舟迎送海内外游客 探访都市村庄 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以生产粮食为职业的劳动者,是9亿多农民。农民是中国这爿蓝色天空的擎天大柱。 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至今已经28年。针对改革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和阻力,自19
毫无疑问,“新农村”将成为2006年的中国“关键词”。从今年起中国全部免除农业税,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到3397亿元,将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设施等公共事业的发展。 中国之大,各地农村的发展水平之差异不能以道里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上海”这个符号似乎与农村、农民和农业离得很远。 其实不然。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团队在上海郊区农村进行了整整半年的实地调查。今天,我们摘要发表他们的调查报告,随他们一同走进都市村庄。 都市农民身份谜团 在上海郊区,一些农民既是“地主”又是“雇工”,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大地实现了土地的价值,提高了经济收入,这是一种“曲线务农”。 今年春节刚过,一个早上,奉贤J村的一群当地妇女正在阳光下分拣和清洗刚刚从田里拔起的青葱。这些葱的主人是谁呢?她们说:这是一个外地人租用本地人的农田种植的,为了卖一个好价格,需要分拣,剔除黄叶腐根,并洗去根部的泥土。洗葱这样的活是一斤2毛钱,她们就是冲着报酬来干活的。这些土地的主人又是谁呢?几个妇女说,她们就是这些土地的承包者,也就是土地的主人。 她们是土地的主人,同时又是打工者。事情似乎有点糊涂了:在经济活动当中,她们究竟是什么角色? 困惑油然而生。出租土地者,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地主”,而租用土地耕种或在他人土地上临时干一些活的人被称作“佃户”或“短工”,当年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一个平时靠打短工维生的农民。阿Q这一类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往往处在最低的社会阶层。然而在今天上海近郊的农村,居然出现了集“地主”和“短工”于一身的社会角色,其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土地出租可以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为何“地主”还要去打工?如果土地上获得的经济收入可以付得起打工者的工资,那么为什么土地所有者自己不去耕作,从而获得比打工更多的经济收入?是什么割断了土地所有者自身与他们所有的土地之间的关系? 调查慢慢解开了谜团。刘大娘的一笔账解开了其中的奥秘。她家共承包3亩地,自留地4分。以往承包地用来种植水稻,每年收入不过700元左右,而这点钱“正好冲掉种地的肥料钱,没什么多余的”。 账是这样算的:下种前机器犁地70元/亩、机器割稻50~100元/亩、肥料150元/亩(3包)、打药水100元/亩、雇人插秧70元/亩。如果劳力全部自己投入,省去雇人插秧和机器耕种的话,一亩地最少也要250元,3亩地也要750元的成本,几乎没有什么盈利。 所以今年开始,经人介绍,刘大娘的2亩地租给别人种西瓜,有1800元的收入。地租出去以后有了空闲,刘大娘和老伴都给外地老板打工。她帮人家洗葱,每斤2毛钱,一天可以有10到15元的收入。据了解,这也是当地很多人的赚钱方式。由此可见,一些人正在同时扮演“地主”和“雇工”的角色,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所概括的“经济理性”。 那么,租地的外地人靠什么赚钱呢,他们正在干的事情,有什么是上海的农民不能干的吗?难道上海的农民不能用同样的方式获利吗? 目前土地制度和使用方式可以解开这些问题的症结。农村土地法律上属于集体所有,使用上实行的是“30年不变”的承包制度。按农户家庭人口多少分配承包土地是目前土地获得与使用的基本方式。上海郊区人多地少,一些地方一户家庭只有几分地。在目前化肥、农药、电力等价格都逐年上涨的情况下,种田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前几年粮食价格又连续下降,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谷贱伤农。地少,在经济上没有规模效益;投入大,缺乏投资效益;谷贱,则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 调查发现,有些农民将承包的土地退还给村管理委员会,由村里出租,退还土地的农家获得每亩每年500元的收入。这样的活动是以村委会和农户之间签订合同的形式确定的,最长的合同年限也是30年。这实际上是一部分上海农民对土地和农业的放弃。 而外来人员则不同。他们使用土地不受按照家庭人口多少的限制,只要你按时交付租费即可,在土地上种什么也不受干涉,只要赚钱就行。在一个村中,一个安徽人在村中一下租用了60亩土地,规模效益由此充分体现,一年有几万元的收入,并可雇佣村里的居民工作。在上海市场,葱最贵时每斤4元,这使得外来“佃户”又变成了雇佣“地主”的“雇主”。 土地是农业的根本,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重视。在土地上,只要你辛勤耕耘,就一定会有收获。俗话说“土地是不会骗人的”。但也应该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农业已经划分成两种不同的现实形态。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土地主要是获得基本生存资料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获利的形态。在农村这样的自然聚落中,农民经过男耕女织的方式,从土地中获得衣温食饱,即便是那些出租土地的地主也基本如此。几亩地,一间房,曾经是多少中国人的梦想。 这种传统的农业形态曾经是农业经济的全部解释。但这样的解释毕竟已时过境迁。在今天的世界上,农业已经像工业一样,成为一个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经济价值的领域,市场、规模、投资、技术、经营、效益同样成为衡量农业活动的标尺。维持自我基本生存的农业经济形态已经成为过去。同时,在农业经济活动之外,现代社会又提供了实现个人劳动力价值和土地价值的其他方式,不仅职业活动可以使人们摆脱土地获得生存,而且人类自身的扩张,如工业和城市等活动与形态又在不断提高土地的价值。在地球上,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世界各国都把土地储备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储备。 在上海郊区,一些农民既是“地主”又是“雇工”,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大地实现了土地的价值,提高了经济收入,这不能不看作是他们对当前农业土地制度的一种突破,突破了种地仅为吃饭的单一经济意义。这种突破是以放弃直接从事农业和土地开始的,是一种“曲线务农”。 既然小规模的土地耕种和运作已经不能负荷农民的经济希望,既然土地实际上还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既然农民可以以一种职业雇工的形态参加市场化的农业经济活动,那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目前的农业经济方式和土地使用制度是否符合现实的经济生活,这种形态与现代农业经济有何不同。反思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这是一种经济形态的全面改变,同时也呼唤着农业经济地位的重新确定和新的土地使用方式的出现。 招商喜忧:袋里有了钱,河里没了螺蛳 如果完全让农民自己构成的村级集体形式来争取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条件,这是否公平呢? 近十几年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农业集体经济似乎已经名存实亡,好像土地承包制度开始后,人民公社变成了镇政府、生产大队变成了乡政府、生产队变成了类似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村民委员会,那些“队为基础,独立核算”的集体经济实体好象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在上海,农村集体经济依然存在,而且已经成为实现目前农村发展和农民保障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 让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嘉定与奉贤几个农村集体经济的现状:嘉定T村,村中共有500多户居民,土地大多已成为开发区,村集体有33个村办企业,年工业产值在2亿元左右,村委的年收入在200万元左右;M村,全村不到700人,年工业产值有5亿多元;S村,约2270人,土地大多被征用,仅剩200亩用于农业耕作;奉贤J村,集体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厂房租赁,平均每年的固定租赁费能收到160多万,本村还有其他500多万元收入。 村级经济承担众多的社会事务,用村干部的话说:“村干部工作有‘八条线’:行政、民政、司法、卫生、治安、工会、民兵、调解,基本上涉及到各个政府部门的任务。本来村委会像居委会一样,是群众自治组织,但实际运作上往往与政府部门各个条线相对应。” 以某村为例:集体经济虽然一年有200万元收入,但老年人的养老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很大(有的村每月支付每一位老年人养老费用180元,有的村标准为250元)。过年过节往往是村级经济大支出的时候:每年重阳节一下子就要花掉4万到5万元,春节送温暖也需要大笔花费。实际上村级福利基本全靠村委提供。 发展集体经济是村干部的头等工作,而且村级社会福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村干部的选任,在上海郊区农村,村干部已基本上由当地居民提名和投票。村委会的首要工作是发展村级经济,包括招商引资、出租厂房、出租农田等,因为“没有钱什么事都做不成”。 今天,农业经济在村级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不复当年。在一家村委会的会议室中,有一张经济现状和规划表,其中200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8亿,利润300万,农业总产值仅为260万,利润只有80万。今年的工业利润计划比去年增长60%,而农业利润计划只增长10%。这种发展数字的差异揭示了一个现象:农业生产增长不像工业经济一样,每年都能上新台阶。试图通过农业实现目前村级经济所承担的各种社会福利事务是不可能的。在与村干部座谈时,谈到发展经济,村干部们说的都是“招商引资”、“招商引税”、土地开发、厂房出租、乡镇企业改制租赁,几乎没有一个人谈到农业发展和土地的基本建设。 现存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能够保证每年利润或收入的增长,但它的不利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是农业土地的减少,造成短缺性资源的永久损失;二是环境的破坏和失衡,工业集中的一些村子里,由于缺乏环保设施与管理,河道水质往往污染严重。一户农家主人津津乐道地谈起二三十年前在大田和河中抓螃蟹的事,如今只有一些小龙虾了。一户农舍边的小河发出难闻气味,而在20年前,这里还可以下河“拷鱼”,摸到下酒的螺蛳。三是人们的心思都转移到“打工”这样的职业活动上去,农业耕种成为一种“业余活动”,农田基本建设多年来很少有人关注,灌溉设施陈旧不堪,土壤质量连年下降。四是一些村干部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权力过大,以致个别地区干群关系恶化。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农业、农村、农民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物质和人力等几乎一切必要资源,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前提,但自身获得却甚少。在强势的工商业经济面前,如果完全让农民自己构成的村级集体形式来争取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条件,这是否公平呢?- “农村户口”在新浪潮中消失 不管城乡户籍是否存在,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中,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浪潮将把这两种身份的人融合在一起。 在中国农村,造房子是一件大事,人们往往为此花费毕生劳作的积蓄,奠基、上梁时还会有一系列隆重的祈求吉祥的仪式。在农民心里,房子意味着财富、脸面、地位和子孙绵延。为儿子盖一套房,是媳妇进门的基本条件,也是父母的基本职责。村落随着建房而不断延续和扩张,农民的身份也随着房子的继承而代代相传。 所以,房子可以看作农民的根基,是农民与土地息息相关、血脉联系的中介。 2004年的农村问卷调查发现,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上海郊区农民建房的高峰期,此后却少有农民自主建房。当然,当时建房的费用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当年一栋两层约200平方米的房子大约只要几万元钱,调查显示当时房屋的平均造价为28553.76元,每平方米的平均造价为135.7元。 今天农民不再建造房屋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造价高了吗? 访问一户户农家时,在显得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居住的往往是年龄50岁以上的中老年夫妇,很少有年轻夫妇与父母住在一起。在一些工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一排排房子中居住的是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外来居民,管理这些房客的也往往是一些老人。中青年人到哪里去了? 在上海的一户农家,主人家庭的状况是这样的:男主人及其配偶现年均为50多岁,身体都算健朗。生有一女一男,均为初中学历。女儿在镇上的工厂里上班,女婿是出租车司机,外孙女已上小学。儿子与儿媳同在镇上的一个服装厂里上班,孙子上幼儿园大班。男主人18岁时就进了乡种子厂,一做就是23年,26岁那年在厂里入党,后来成为厂长。此后他又在乡电镀厂干了10年。1990年代初期电镀厂倒闭,1200元买断工龄后,他辗转进了小舅子开的一家针织制衣厂,至今已有6年。男主人最得意的事就是在1994年时花了11万(积蓄加上借款)买了一间商品房,现在儿子正享受着他置下的这份财产。他表示村里的农户八成以上也都在镇上买了商品房(多少都有亲友借款),而且都是在1990年代初期房价较低时买的。现在有的家庭为房子发愁,因为子女结婚不愿意住在自己造的房子里,有的儿子要求父母在镇上购买房屋,否则就不结婚,要挟老子“以房子换孙子”。 在村干部座谈会上,当问及家庭居住状况时,不少村干部表示居住在镇上的商品房里。一位村干部原有的80年代建造的房屋,现在大部分已出租给外地人,300平方米每月租金1800元左右,他和他的子女也全部迁入镇里居住了。 2004年的调查发现,在农村居住的人中,22%的人口超过60岁,50岁上下的人口接近50%,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员占当时调查全部家庭人口的16.55%。这样的一种人口结构表明大量青壮年已离开了家庭。 即使居住在当地的人,大多数从事的也是职业活动。在本次访问的大多数家庭中,绝大部分人员并不从事农田耕作,而是有固定收入的职业活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几乎没有从事农业活动的。由于过去几年从事农业活动几乎没有利益可言,人们已经把土地托付村管理机构转包给他人,并从这种转包中获得仅能抵消家庭粮食消费的收入。实际上土地又出现了一种集中,这种集中意味土地出现了名义使用权和和实际使用权的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已经不是农业活动,而是某种职业获得的工资收入。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已经远远不如过去亲密,不少农民的后代甚至已经远离土地。 农民与土地之间隔膜的出现,早在80年代就开始了。80年代是农村大办集体企业的年代,是乡镇企业崛起的年代,许多农民放下锄头拿起榔头。但当时大多数农村家庭还是兼工兼农,而且当时乡镇企业的集体性质,也使得当时的农民依然依恋本土本乡,根在土地,房在农村。 90年代后上海的城市和工业扩张浪潮席卷了整个上海农村,不仅大量的土地征用把众多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而且更多的人在多元化的经济活动中自觉地改变了农民身份。他们一旦从事职业性的经济活动,就可以自由寻找自己的居住空间,从而变为一个漂浮的个体经济动物。农民与居民、建房和买房,实际上是从事两种不同经济活动的人的两种不同的居住形态和生活形态。 从21世纪开始,上海市政府规定,在上海郊区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任何21世纪后在上海郊区出生的孩子,将只有一种身份标志,就是上海户籍人口。这实际上是对20多年来农民身份逐渐变更的承认和肯定。不管城乡户籍是否存在,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中,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浪潮将把这两种身份的人融合在一起,这种身份的融合和更改,是人们在生活中自觉实现的,而政策往往是滞后和被动的。-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