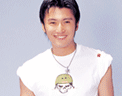“问题举报人”乔松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14日15:35 新民周刊 | |||||||||
|
“问题举报人”乔松举 就在乡邻们猜测着有关部门将如何嘉奖乔松举时,11月24日深夜,乔松举被高邮市天山镇派出所从家中带走“问话”,第二天,家人接到了他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的通知,理由是涉嫌两年前的一起敲诈勒索案。
撰稿/杨 江(记者) 举报之后的拘捕 12月7日,一股自北而来的冷空气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苏北腹地的高邮市初见薄冰覆地,傍晚6点,高邮市郭集镇盘塘村已被浓浓的暮色笼罩,一阵“咔咔”的金属撞击声自远而近,51岁的鹅农马正朝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到家中。 马正朝的家是三间已经破败的瓦房,裂痕爬满墙壁,他推开虚掩的木门,因为墙壁透风,屋内并不比屋外暖和多少,昏黄的灯光中,妻子王素琴正在做晚饭。马正朝嘴里呵着白气,猛搓着被冻得通红的双手,“前后两家邻居都是楼房,我家太寒碜了,您别见笑!”他尴尬地跟记者打招呼。 10月24日,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安徽省天长市便益乡梁营村发生一起H5N1亚型禽流感疫情,首先发病的正是马正朝在梁营村稻田内放养的1000多只鹅。“原本指望这批鹅帮我翻身,谁想到老天爷这么不帮忙,让我倒这么大的霉。”马正朝嘀咕,“灰溜溜跑回高邮,都不敢跟乡亲们说,怕人家笑话。” 尽管农业部迄今为止仍未公开证实,马正朝的好友乔振泉的小儿子乔松举到底与天长市的禽流感疫情的发现有着怎样的联系,但从天长到高邮,在一些政府官员私下言谈与民间议论中,“乔松举是举报人”俨然已成一个公认的事实。 “就是乔松举把我的鹅发病的情况举报给农业部的,他觉悟比我高,因为上报及时,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所造成的损失也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马正朝证实。 也正因此,乔松举,这个31岁的高邮市天山镇农民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因为乔松举的举报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马正朝还是为乔松举高兴。 在由中央电视台发起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凭借“第一个向农业部举报禽流感事件的民间人士”的身份,乔松举被列为52名媒体推荐候选人之一。 几乎所有对乔松举的评价都在不断强调着他“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比如“一个普通的农民,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敢,把事实和真相及时反映给政府,避免了一场类似四川猪链球菌事件的重演”。 还有评价说:“尽管他的举报让当地养殖户损失惨重,让当地政府面对农业部感到尴尬,但在禽流感肆虐之时,一个普通农民的担当仍然让许多人为之感动。” “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不凡的壮举!”有人直言不讳,这样的强调,想要勾起的不仅是大多数人对乔松举的敬佩,还是让一些人脸红。 这些内容,马正朝从家里的那台黑白电视和记者带来的报纸上看到了:“他值得这样的表扬。” 然而,就在乡邻们猜测着有关部门将如何嘉奖乔松举时,11月24日深夜,乔松举被高邮市天山镇派出所从家中带走“问话”,第二天,家人接到了他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的通知,理由是涉嫌两年前的一起敲诈勒索案。 乔松举自此未能返回家门,“是否因举报遭受打击报复?”一时间,议论纷起,也将高邮市公安局推入舆论的漩涡。在缄默近两个星期之后,高邮市公安局于12月7日通过《扬子晚报》向社会发布消息,大意是,乔松举以向农业部举报非法生产禽流感疫苗等为名,多次敲诈勒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当地警方还一并透露了乔松举几次“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至此,禽流感“第一举报人”乔松举被捕成为了议论四起的事件,记者再次云集高邮。 当天报纸上的内容马正朝没有看到,他舍不得花钱买报纸,因此,进屋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扬州的电视台报道了乔松举“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 马正朝懵了,他赶紧给乔振泉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样的沉闷——乔振泉在赶往马正朝家的路上听说这个消息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这就算定罪了?根本没有的事啊!” 接下来的几天,《新民周刊》在对高邮市多个政府部门、“被敲诈单位”及近20位知情人士的走访后发现:乔松举举报禽流感并非此前他本人向各界所宣称的——“偶然”!而他的身份也似乎并不那么“普通”!“敲诈勒索”也扑朔迷离。 举报是因“身负其责” 20多分钟后,等王素琴把晚饭烧好,乔振泉也到了,一大海碗热气腾腾的炖鹅被端上桌,“这可不是从安徽带回来的病鹅!”马正朝抿了一大口酒,乔振泉则一口接一口猛吸烟。 高邮位居南京后方,受赐于广袤的高邮湖,成为江苏有名的鹅乡、鸭乡,南京地区的盐水鸭原料多来自高邮,而高邮咸鸭蛋则更是享誉全国。马正朝与乔振泉正是在养鹅中相识成为知己,两人都是有10多年养鹅经验的“老把式”。 上个世纪80年代,高邮鹅农放鹅还局限在高邮境内,1990年代,一部分鹅农、鸭农开始将鹅、鸭运至邻近的安徽省天长市放养。从地图上看,天长市像一个拳头一样嵌进江苏,周边三个接壤城市是江苏的扬州、高邮和六合,因此与江苏往来频繁。 高邮与天长都产水稻,因此每年收割水稻后,高邮的鹅农都将成千上万只鹅、鸭运至天长,在稻田中放养。“鹅、鸭散养在稻田里,吃掉在地里的稻谷,节省了饲养成本。因为散养,肉质又好,南京人最喜欢吃这样散养的鹅、鸭。”马正朝说。1994年,他第一次在天长放鹅,今年9月,他又从山东买回了1200多只鹅,每只30元,加上路费花去了3.6万多元。 这是马正朝第三次到天长放鹅,鹅买好时,天长市正值稻谷收割,他便将1000多只鹅直接从山东运到了天长便益乡梁营村,同样来自高邮的黄安国夫妇也买了600多只鹅。因为黄安国夫妇养鹅的成本是向马正朝借的,因此两家将鹅放养在一起,“鹅放养在稻田里,我们就在田埂上搭个棚子,晚上就睡在棚子里看鹅。还雇了一个当地人,每个月工资给450元。”马正朝说。 10月6日,马正朝早上起来,1000多只鹅已经在稻田里啄食,他突然发现有两只鹅落单了,在田里绕着脖子打转,“眼角有分泌物,翻着白沫。我没有多想,养鹅的都知道,死几只鹅并不奇怪,我就把其中一只鹅杀了吃了,还有一只因为很瘦就随地挖了一个坑埋了。” 孰料,第二天一早,马正朝又发现了一只鹅奄奄一息,“我觉得鹅肯定生病了,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是禽流感,因此还是挖了个坑埋了。”忐忑中,马正朝给高邮市兽医站一个姓朱的退休兽医打了一个电话,朱兽医与他关系不错,一听就大叫:“不好,可能是禽流感。” 马正朝要朱兽医帮忙给鹅打疫苗,朱一开始不同意,后在马的一再要求下,于8日下午从高邮郭集镇兽医站拉了一批禽流感疫苗到了天长。据马正朝介绍,这批疫苗确是禽流感疫苗,“哈尔滨产的,农业部专家后来也说了是正宗的疫苗。” 但为时已晚,在疫苗打下去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日,鹅开始大规模死亡。“一天就死了十几只鹅,还有很多鹅在水里打转。给鹅打针是在梁营村村民毛长巨的家中,结果,毛家的鸡也开始大批死亡。” “我很慌,又不敢向政府汇报,听说禽流感是很严重的疫情,虽然死了鹅,可我不敢断定是不是禽流感,要是查下来不是禽流感,追究我乱说,怎么办?再说,向哪个部门反映?反映了有用没有?”马正朝坦言,“我怕我的鹅被扑杀了得不到补偿,血本无归,所以也不敢反映。” 在14日乔松举将马正朝的鹅大规模死亡的情况向农业部举报之前的4天中,马正朝的鹅继续大规模死亡,“最多一天就死了100多只。”马正朝惶恐不安,他以泪洗面,一个人在晚上看着死鹅落泪,不敢告诉在高邮家中的妻子。 为了减少损失,他开始悄悄自行处置,将死鹅的毛拔下来留着出售,然后继续悄悄掩埋。此时,已经有人想把死鹅肉卤了,因为这个地方和周围城市的人都喜欢吃“卤老鹅”。另外,马正朝开始悄悄联系买家,准备将没有死的鹅卖掉,他联系了高邮的一个王姓鹅贩子,对方不敢买。 而正是因为他急欲卖鹅,消息才首次传到江苏,乔振泉当时正在江苏境内放鹅,他给马正朝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就哭了。很可能就是禽流感,死鹅千万不能乱埋,更不能卖到江苏,一只都不能。你也不要难过,果真是禽流感,国家会给你赔偿的。” 马正朝不敢再拔鹅毛了,将几百只死鹅堆在田里,用草盖上,“不敢告诉安徽人,怕人家笑话。”而乔振泉也赶紧给三儿子乔松举打了电话。“乔松举在农业部认识很多人,我们家只知道他是农业部的信息员,我要他问问农业部,如果是禽流感有没有赔偿。”乔振泉说。 “三子(指乔松举)当时就说,不管是不是禽流感,也不管马正朝是不是咱们家朋友,我都要向农业部汇报,我是帮部里做事的,这事发生在我附近,我有责任举报,如果隐瞒,部里查下来我没法交代。”乔振泉告诉记者。 一边,乔松举开始搜集线索,一边,马正朝开始在他的要求下于10月14日一早拎着两只死鹅赶到天长市畜牧兽医站汇报。“兽医站的人正准备解剖时,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江苏高邮的,在这里放鹅,一个20多岁的女同志就说,高邮的怎么跑到我们这里,赶紧到扬州农学院去化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技术水平。” 马正朝只好怏怏地又拎着死鹅回了梁营村。他没有去扬州,因为他觉得去了是一样的结果,这天,鹅死得更多,他已经开始准备自己吞“苦果”。因为按照有关扑杀家禽的政策,补偿费远远不能弥补养殖户的损失,于是他偷偷将一部分病鹅卖到了天长市的秦楠镇。 幸运的是,他把在天长兽医站的遭遇告诉了乔松举,而乔松举在10月14日上午9点左右,也就是农业部刚上班不久,就将电话打到了农业部兽医局。“本来是找局长的,局长不在,就告诉了秘书。”乔振泉说。迄今,农业部并没有公开证实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农业部迅速作出反应,一小时后立即决定派调查组去安徽。当天夜里,农业部的专家赶到了天长。“乔松举是农业部的民间信息员,他一直在帮农业部打击假疫苗,农业部还给他报销飞机票、出差费,所以他能直接找到农业部的领导,人家也相信他反映的情况。”乔振泉透露。 “好处费”风波 乔振泉向记者证实,儿子乔松举在被高邮警方刑拘之前一直在刻意隐瞒自己与农业部的关系,以及举报禽流感信息的真正动机。在乔松举“第一举报人”的身份被披露后不久,乔松举就表示,自己之前没有做过类似向上面反映疫情的情况,这次是偶然知道的。而之所以与农业部联系是因为“去年看到禽流感闹起来的时候很多养殖户损失很惨,而且另一方面,已经了解到马正朝已经准备把病鹅往江苏卖。” 乔松举把自己的举报解释为情急之下的举动。11月14日,他在北京见到了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事后他对媒体表示自己拒绝了农业部的奖励,“如果国家能全额补偿,保障养殖户的利益,就用不着我来举报了。因为补偿远远不能弥补养殖户们的损失,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主动反映疫情。” 乔的言语中,对于举报的动机似乎也有不少无奈的味道。但12月7日,马正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描述却表明,乔松举与农业部似乎“关系密切”。 马正朝说,农业部专家赶到天长后,在对他所养的鹅做扑杀和补偿工作中,乔松举一直担当着“协调员”的角色。 10月14日夜里11点多,天长市有关人员就赶到了梁营村,由于扑杀家禽后给予养殖户的补偿费由地方财政支出,同时,疫情的披露也将影响地方经济,农业部调查组的到来给天长市的一些官员造成一定压力。有人马上找到马正朝,质问“为何要直接报到农业部”,还提出给他一笔钱,想赶在农业部专家到来前扑杀病鹅,让他立刻离开天长。 “来了不少公安,黄安国的老婆一看就吓哭了,以为自己犯了很大的罪,躲到了毛长巨家里。”天长市的官员走后,马正朝在电话里问乔松举,那些鹅被杀了之后有没有补偿,乔说有,马正朝又问,能不能全额补偿,天长市的官员告诉他每只鹅国家只赔6元,所以劝他拿着市里给的钱走人更合算。 实际上,按照国家规定,一只鹅赔偿15元,而按照疫情发生前的市场价,一只鹅能卖到30元。乔松举在电话中嘱咐马正朝不必担心,因为农业部的人已经到了。 15日早上6点多,天长市政府又派人进村与马正朝协商扑杀补偿,“他们说按照规定只能补偿15元一只,我一听就急了,一只鹅的成本都要30多元,我不亏死了嘛。” 马正朝不肯扑杀,谈到20元一只,马正朝还是不答应,他回答天长方面的人员,“农业部已经来人了,如果是禽流感,肯定会给我们一个说法。”按照马正朝的介绍,他说出这番话后,天长方面将补偿价格提到了40元一只,要求立即将存活的1500多只鹅全部扑杀。“我给乔松举打了电话,他说扑杀是肯定的,农业部领导马上就会带人到现场。” 马正朝说,农业部领导果真如乔松举所说的给他打了安慰电话,并在8点左右出现在他面前。农业部专家在忙着解剖、取血样,马正朝担心得不到合理补偿正站在一边哭泣。“农业部领导看到我们放鹅的晚上睡在田埂上很不忍心,说如果是禽流感肯定会妥善解决。” 马正朝心里有些底了。农业部专家取样回城后,乔松举也从郭集镇打车赶到了现场,“他让我放心,说会向农业部反映我的困难,呼吁合理补偿。”随后乔松举赶到了天长市,向农业部调查组汇报了他所知道的情况。此时,马正朝才将鹅发病大量死亡的情况在电话中吞吞吐吐地告诉了高邮家中的妻子王素琴,王素琴一听就号啕大哭:“这下冲家了。” 扑杀补偿没有谈妥,鹅没有被扑杀,马正朝在这天下午还买来了几百元稻谷喂存活的鹅,“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检查下来不是禽流感,我就继续养,免得损失更大。”但一个下午,马正朝又眼睁睁看着100多只鹅在他脚下死掉。马正朝几近绝望。 当晚便益乡有关领导前来要求扑杀,马正朝不肯。“天长市农经委于主任来了,谈到25元一只,我还是不同意,我给乔松举打了一个电话,他劝我们不能太过分,要以大局为重。后来于主任说一只补偿36元,我想想答应了,黄安国的老婆不答应,我还劝服了她。” 扑杀人员忙着挖坑,将活着的鹅赶到坑中,马正朝泪流满面,不忍目睹,便跑到田埂上散步,黄安国的老婆一直哭到天亮。 “于主任打了一张6.6万元的白条,叫我17日领款,说实话,我多报了250多只,后来去领钱,我承认多报,于主任说不追究。”天长方面提出要马正朝他们住在天长观察20天,宾馆费用由天长承担,但马正朝因为耳边仍不时响起鹅的惨叫声,急着离开伤心地。 “看到我们吃不下,睡不着,于主任就派车把我们送到了高邮家中。”马正朝认为,如果不是乔松举,他也得不到这么多补偿,因此想送给乔2000元,“我提出给乔振泉,乔振泉骂了我!乔松举还指责我多报养鹅数量是不对的。” 乔松举的妻子王秀兰也告诉记者,乔松举为举报天长的疫情,交通、通讯花了1000多元,“乔松举没要马正朝的钱,他告诉马正朝,所有的费用农业部会为他报销的。” 马正朝回高邮后不久就去了河南,他想再买鹅回来养,在河南期间听说了天长禽流感疫情确诊的消息,他马上赶回了高邮。 2000元好处费没有给出去,消息却已经传遍了高邮,“乔松举肯定得了不少好处,不然不会举报。”不少人猜测。 10月26日,马正朝在农田里被郭集镇派出所民警找到,并被带到了高邮市公安局,马正朝对着记者的录音机复述了当时的部分问话。 “在天长拿了多少钱?” “六万六千元。” “就这些?不止吧!……钱给哪些人了?” “没有给别人。都在我这。” “那乔松举的钱呢?给了多少?” 马正朝回忆,当时高邮警方反复问了他“乔松举为何直接举报给农业部”的情况,等问话结束已是深夜,他提出这么晚无法回乡下,公安局一名领导便借给他30元住宿费,让他在县城找个旅馆住下。 那晚高邮下着大雨,马正朝觉得委屈,泪流满面,一个人在街上散心,淋了很久的雨。 他事后才知道,同一天,黄安国夫妇、乔振泉、乔松举都被叫到高邮公安局“问话”,内容几乎一致。 乔振泉也对着记者的录音机复述。 “警察问为什么直接向农业部举报?举报是什么目的?” “我说应该举报,否则对人生命有损害。” “姓马的给了你多少钱?” “没有,我要是拿了一分钱,我负责。” 而乔松举后来也向媒体透露了警方讯问的内容:“你拿了农业部多少钱?是谁让你举报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 乔松举的回答是他从没拿过农业部一分钱奖励,也没拿过别人的好处费。“后果很严重?是不是乔松举被捕就是这个的后果呢?”12月7日,乔振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忿忿不平地问。 郭集镇的疫情 尽管满腹委屈,乔氏父子在接受讯问回家后并没有过多声张,“我们当时一直很低调,隐瞒了乔松举和农业部的关系,是因为害怕受到报复,乔松举以前向农业部举报过扬州地区很多假疫苗地下工厂,但是乡邻们都不知道。” 马正朝说自己灰溜溜回到高邮,再也没有与天长那边的便益乡有过一丝联系,他从报纸上看到,梁营村的村民对他很有意见,认为是他这个江苏人将病情带到了天长,害了天长。而毛长巨一家也觉得无脸面对乡亲,“因为几个高邮人是住在他家的。毛长巨的老婆张和平一度躲到娘家,理由是“怕村民白眼”。 马正朝获得了超过标准两倍的赔偿,但便益乡的其他村民却没有这么幸运,为了控制扑灭禽流感,天长市扑杀了便益乡梁营村3公里范围内的4.5万多只家禽。天长市对被扑杀的家禽补偿标准是:鸡每只10元,鸭每只12元,鹅每只15元。 因此,村民们多有损失,“高邮人举报了禽流感,拿了钱就走了,却害惨了我们”。在农村,养鸡户家里死几只鸡很正常,常送给乡邻吃。在梁营村,至今仍有百姓认为,如果乔松举不举报,疫情并不会扩散,举报反倒把事情闹大了。 高邮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乔振泉也听说,天长那边的百姓表示以后不会允许高邮人再到天长放鹅。不过,乔松举在高邮并没有受到如此之多的民间“讨伐”,人们仍在猜测他到底会得到怎样的嘉奖,甚至有人认为“钱早就被他装到兜里了,他不可能告诉大家”。 乔松举到底有没有拿到奖金,除了他自己表示过曾拒绝了农业部奖励外,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证实过。但不管怎样,乔松举举报禽流感的事情渐渐过去,人们开始渐渐淡忘,乔松举也以为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放养了几百只鹅在天山镇,后来被赶到了仪征,虽然在天长发生禽流感疫情后很快就由兽医站打了疫苗,但是却一直拿不到防疫证。”乔振泉说,他一直在向高邮市兽医站索要防疫证,但兽医站就是不肯给。 “没有防疫证,鹅就这样被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回不了郭集,现在天越来越冷,鹅散在仪征,我每天都要跑很远去看鹅。” 乔振泉说,乔松举为此多次到兽医站理论,甚至好几次吵得不可开交。“11月中旬,高邮郭集镇也发生过一次疫情,是不是禽流感我不知道,反正扑杀方式和禽流感一模一样,也没有公布。”乔振泉说,乔松举也向农业部举报过,“不知道被捕与这次举报有没有关系。” 郭集镇发病的鹅是养殖户顾万里家的1000多只鹅,11月17日开始发病,先后死了100多只,马正朝说,顾万里在18日给他打了电话,透露每天都要死二三十只鹅。“我听他介绍,与我的鹅症状差不多,就建议他赶紧通知高邮市兽医站。”马正朝说。 对顾万里家的鹅的扑杀在11月22日夜间进行,当天中午,马正朝还被叫到郭集派出所问话。“派出所问我有没有打电话给乔振泉、乔松举,我说没有。”记者对这次“疫情”进行了调查,顾万里已经不在家,他的老婆对记者的提问一连几个“不知道”,甚至连连摆手表示不认识乔氏父子。 不少村民证实,自家的鸡鸭均在22日夜里被扑杀,不过得到了补偿。记者在村口道路上发现了当时的消毒哨点,而在高邮湖边,也发现了郭集镇扑杀掩埋家禽的现场,煞白的石灰粉到处都是,两名正在现场负责消毒的农民证实前一阵子郭集镇扑杀过一批家禽。 “方圆3公里的所有家禽全都被扑杀了。”有村民透露,当地政府称不是禽流感而是热性传染病,顾万里的妻子认为不是禽流感捕杀后就不能得到补偿,因此想卖鹅,但遭到阻拦,于是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幸被抢救过来。 12月9日,高邮市农林局生产科科长陈林祥向记者承认,郭集镇的确发生了“热性传染病”,“是农业部确诊的。” “我们在天长发生禽流感疫情后就立即给全市的家禽注射了禽流感疫苗,但是11月17日我们得到消息说顾万里家的鹅发病了。工作人员觉得很奇怪,不是免疫过嘛。一问,才知道顾万里从天山镇郭兆军家又买来了43只灰鹅。” 陈林祥说,正是这43只鹅导致了顾万里家的鹅的发病,经过追查发现,这43只鹅是乔松举带着顾万里去买的。“他既然能举报禽流感,就应该知道在禽流感期间介绍人家买卖家禽会导致疾病传染的危险。”陈林祥认为乔松举对郭集镇的疫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制造疫情。” “为防止禽流感乘虚而入,我们采取了极端措施,虽不是禽流感,却按照禽流感的扑杀方式进行,宁错杀三千,不放走一个。高邮市委书记当晚就拨款60万元,用于扑杀,总共花费69万余元,如果乔松举不介绍人家买鹅,就不会造成这个后果。” 郭兆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鹅的确是乔松举带顾万里来买的。”但乔振泉却表示是他的大儿子乔松青介绍的,他怀疑郭兆军受到压力说了谎话。 郭兆军有些气愤,他回答记者:“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我问你,即便是乔松举介绍的,又能说明乔松举什么呢?我和乔松举认识,他为人可以。再说,我这又不是疫区。” 高邮市畜牧兽医站倪兆朝站长对记者表示:“陈科长可能不太了解情况,这次热性传染病不是这43只鹅导致的,与乔松举也没有关联。我可以为这话负责。” 陈林祥说,他不清楚乔松举是什么时候将郭集镇的情况举报给农业部的,总之,给高邮带来了很大的损伤。 乔振泉告诉记者,乔松举在11月24日上午为防疫证一事到高邮市畜牧兽医站吵过后,就向农业部举报了高邮的“疫情”。 就在这天夜里,高邮警方在乔松举家中将其带走,“我、乔松青、还有我女儿都同时被从各家带到了公安局。”乔振泉说,此前高邮畜牧兽医站有关领导还曾找他要求他让乔松举不要举报高邮的疫情。一旦被当作禽流感处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就不得了。 敲诈勒索? 12月8日,在高邮市天山镇,乔松举的爱人王秀兰向记者介绍了乔松举被警方带走时的情况。11月24日晚10点多,正在家中的乔松举接到来自高邮市公安局的电话,要求乔立即到高邮市公安局一趟。乔称“太晚,路又远,第二天再去”。 “对方说,不行,要与你处理问题的,否则你要上报。”王秀兰回忆。不久,乔松举接到天山镇派出所所长打来的电话,叫他出来了解情况。所长当时就在乔家楼下。王秀兰不想让丈夫出去,乔说,“没事,我没做违法的事情,怕什么!”。 “走之前,小乔对我说,高邮发生了疫情,我向农业部反映了。”王秀兰回忆,“他还说,如果他明天早晨不回来的话,我就给农业部打电话,我说我没有号码,他就把农业部兽医局贾幼陵局长和秘书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王秀兰辗转难眠,凌晨3点的时候,警察又来了,搜走了乔松举的的通讯录、名片、票据等物品共22件。王秀兰问,乔松举到底犯了什么罪。其中一位负责人回答说,乔涉嫌卖假药。第二天一早,王秀兰没有等到丈夫回家,她拨通了农业部贾局长的电话,将乔松举被警方带走的情况做了介绍。 “贾局长证实天长和高邮的疫情都是乔松举举报的,我担心他是因为举报受到打击报复,贾局长表示果真如此,农业部会说话,但现在是司法机关介入,暂时不便插手。我问乔松举到底和农业部什么关系,贾局长说帮助农业部打假,但是没有工资,车旅费是报销的。” 不久,王秀兰接到了乔松举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面写着乔涉嫌敲诈勒索,她听说,公公家也被警方搜查过,带走了不少物证。 “警方问乔松举与农业部到底什么关系,我说是农业部的信息员,警方说乔松举是以打假为名敲诈勒索。” 乔振泉介绍:“公安局一名领导问我,乔松举为什么要打假?打假有我们地方政府部门,有我们公安局。乔松举为什么不向公安局汇报,而直接向农业部汇报?!我解释,是农业部要乔松举打假的。” 记者在高邮期间一直试图采访高邮市公安局,但宣传科主管领导一直在局外办事,而办公室于科长表示,警方的一切行动都是严格遵照法律程序进行的。 “没有实际证据,警方不可能对他采取行动,现在案情正在侦破过程中,不便透露,能透露的我们已经通过12月7日的扬子晚报向社会发布了。” 记者查阅报纸,公安机关查明的乔松举的犯罪事实为:“以举报非法生产疫苗为名,先后向某家禽科学研究所、某家禽服务公司等单位敲诈人民币4.55万元,并假冒农业部工作人员骗取某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1.9万元。” 乔振泉介绍:“扬州地区有很多疫苗地下工厂,以前,我养鹅因为注射假疫苗导致鹅大规模死亡,曾经向扬州几个单位索赔过。这几笔钱就是因此产生的。 “警方说,那些鹅都是我们故意药死,然后由乔松举实施敲诈的。我发火,说那些地下工厂也害了其他不少养殖户,也赔过其他人。警方说别人是别人,你是你。”针对乔松举的被捕,高邮市农林局生产科科长陈林祥透露了一个细节,他说乔松举曾就高邮的热性传染病疫情勒索过农林局,“当时争吵的声音很大,我在办公室听到了,乔松举说你们不给我钱,我就把死鹅挖出来。后来听说为了息事宁人,先缓一缓,局里给了他两万元钱。” 陈科长强调:“应该是给了,钱都被他放到口袋里了,省重大疫情防治中心驻高邮的一名工作人员知道后认为这已经是敲诈行为了,后来传到省里,才开始对他立案侦查的。” 陈林祥还向记者透露,乔松举当初举报天长市的疫情时并没有说明是在天长境内,而只是说是高邮的养殖户,结果导致农业部专家直接赶到高邮,造成了高邮工作上的很大被动。 “他举报的是天长,不是高邮,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他有意见啊。高邮警方后来把他叫到公安局问话,也是想告诉他,你举报可以,但是不要瞎举报,是哪里的疫情就举报哪里。但现在乔氏父子在制造疫情、制造新闻。” 但陈林祥又表示,具体情况,高邮市重大疫情防治中心倪兆朝站长很清楚,“他深受乔松举之害。”不过,倪兆朝却完全否认了陈林祥有关乔松举敲诈农林局以及举报信息失误的问题,“乔松举即便要闹事也是到兽医站,而不是农林局。陈科长是外围人物,可能不了解,我跟你说的话我可以负责。” 倪站长认为外围对乔松举作了两个极端的判断,其实应该一分为二,“我们鼓励老百姓举报,举报正好可以弥补我们工作的缺陷,求之不得。当然,从常理上讲,可以先举报给高邮市,如果高邮不处理,你可以向上一级部门继续举报。”倪站长说,“但问题是,高邮没有出现举报了不处理的情况啊。” “当然,你说为了及时处理问题,所以直接举报给农业部,这都值得理解,也不是不可。”倪站长认为,“打假也没错,这是老百姓的权利,但是,乔松举据我了解,一开始是好的,后来变质了。” “现在舆论监督力量很大,高邮警方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故意陷害他,之所以对他采取行动,肯定是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具体情况还是应由警方解释。”倪还否认了畜牧兽医站就免疫症“刁难”乔振泉父子的情况。 陈林祥认为,“乔振泉说他打过疫苗了就是打过了?谁能证明?!” “高邮罪人” 12月8日,乔松举的爱人王秀兰聘请的安徽律师孔维钊到高邮市看守所探视了乔松举,乔拒绝“取保候审”,他认为自己没罪。王秀兰也采取了与丈夫一致的姿态。孔维钊的电话几乎被媒体打爆,他说,“警方应该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信息,毕竟,乔松举是禽流感举报人,身份实在敏感,所谓敲诈勒索的单位、细节都应该让公众知道。这也有利于稳定。” “因为农业部至今没有声音,乔松举是否举报了禽流感,以及与本案到底有何关联,都显得扑朔迷离。同时,农业部与乔松举打假是否有关联,现在都没办法证实,而这对案件定性非常重要。” 只有与乔松举关系密切的一些人才在此前知道他是农业部的“信息员”,王秀兰与乔振泉也是2004年春节前后才得到证实他在帮农业部做事。 “以前觉得他神神秘秘,不知道在做什么。有一次,离家一个多月,说是去南京,其实跑到北京去了,我不放心,翻出他的通讯录,上面有农业部好几个电话号码,拨通后对方说,是有一个高邮来的小乔,现在已经陪农业部的人坐飞机到了南京。”乔振泉透露。 “春节前,我陪他去了一次上海,就是为了证实他是不是帮农业部在打假,结果在上海期间,农业部兽医局药政处一个处长果真给他打了电话。”王秀兰告诉记者,乔松举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在家时间很少。 “经常出差,到广东、河南、山东、福建、浙江、上海等地,还总问家里要钱说是买假药送去检验,然后再向农业部汇报。”王秀兰说,今年夏天,乔松举在山东打假期间,还让她给农业部兽医局药政处一名处长发消息求援过。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与部里怎么算工资的,反正没看到他往家里拿钱。”王秀兰说,她还在乔松举的通讯录上看到过乔给农业部兽医局贾局长的一封信的开头,“贾局长,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也是一个养殖户的儿子,我深深地体会到养殖户受假疫苗的痛苦……” “我认识扬州一个姓梅的疫苗地下工厂厂长,乔松举多次举报他,姓梅的后来给过我一次电话,问乔松举到了哪里。这事被乔松举知道了,发了大火,认为这会导致农业部打假的不利,从此再也不肯向我透露半点打假的信息,也不许我再与姓梅的有半点往来。” 乔振泉告诉记者,乔松举对打假行踪很保密,甚至连王秀兰都不知道。“正是因为乔松举多次向农业部举报造假信息,给高邮一些部门带来了很多麻烦。” 现在,乔家期待着农业部能够为乔松举正名,高邮市农林局生产科陈林祥科长却否认了高邮地区存在大量假疫苗的情况。“我们有完整的防疫体制,疫苗都是正规渠道引进的。但是乔氏父子一直不到兽医站领疫苗,甚至还阻止别人到兽医站。专门买问题疫苗,然后鹅打死了就索赔,漫天要价,我们早就多次听说他在做这样的事情。” 陈科长质疑,乔振泉作为一个养鹅老把式,在上了假疫苗一次当后,为何仍一而再、再而三购买假疫苗?对此,高邮市畜牧兽医站倪站长也认为,乔振泉难以解释,即便他不清楚疫苗真假,乔松举也是非常清楚的。 但乔振泉说,“我们是在乔松举帮农业部做事后才知道怎样识别假疫苗,这之前,市里从没有宣传过。再说,以前买了假疫苗,举报后,兽医站都是不了了之,谁还信你们?” 面对媒体及学术界对乔松举广泛的声援及赞赏,陈林祥科长表示,乔是整个高邮市农民的罪人。 “他专门借购假疫苗为名,进行敲诈,制造了不少假疫苗的新闻,也伤害了一些科研单位,特别是对养殖户的市场销售影响很大。就因为他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外面都以为我们高邮有了禽流感。我们的种鸡场,以前,一只鸡苗1.5元,现在一毛钱一只都没人要。” 陈林祥说,人们都不敢吃鸡肉,肉鸡价格从每斤四五元降到了两元,养鸡户每养一只鸡就亏8毛钱一斤。“鸡蛋价格也下降了一元,高邮有一个双河村,50%的农户养鸡,是一个养鸡重点村,原先一家养三四千只,现在最多只养一千多只,有的甚至不养了,鸡崽送给人家都不要。” 陈林祥说,这些都是拜乔松举“所赐”。的确有一些接受采访的养殖户大骂乔松举是农业部的“探子”,“靠出卖乡亲赚钱”。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更多的百姓对乔松举表示出了同情。 人们似乎更相信乔松举是农业部的“信息员”,也似乎更相信他的被捕与“频繁举报”有关。 在苏北一些地区,乡亲乡邻的人情网中,乔松举这样的举报者往往面临很大的压力,有一种叛徒的“羞耻”。比如,在非典期间,倘若有人举报村里某人刚从外地回来,然后导致对方被隔离,往往是要受村民的冷眼的。 有人认为当兵复员后的乔松举这样的举动有些“傻”。“对着干能有好事吗?!”不少老百姓开始盘算向记者透露信息的代价,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少老百姓尴尬地躲避记者。-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