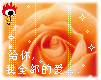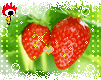| 崔永元:从老电影到精神洁癖(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5日09:43 新民周刊 | |||||||||
  撰稿/李宗陶(记者) 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工作室,坐落于北京一所高校图书馆的四楼。没有电梯,夜晚的楼梯曲折幽暗,直至三楼半出现一块“电影传奇”的铭牌,一切才豁然亮堂起来。门口一副大红对联,“白天忙晚上忙忙活电影;这集好那集好好生传奇”。这语感熟:到老崔的地界儿了。
工作室就一个气质:年轻。走道贴满大大小小的剧照,工作进程表铺满一整面墙,会议桌上乱七八糟,每一台电脑都在工作。挂有巨幅白幕的电影放映间正播一场球赛,冷不丁传来几声高呼:“进了!” 身穿淡天蓝薄毛衣的崔永元跟一长发披肩的小伙子正谈脚本(也就是七八张订起来的A4纸)。他眼圈有点黑,衬衣领子有点皱,可谈得却细,翻纸也慢,一页说完下一页,间或捧起一个大玻璃缸子喝茶,浓浓的沱茶。我坐一旁静等,依稀听明白在说《甲午风云》。崔永元后来告诉我,他跟小伙子讨论的是:一段历史该怎么写。 3月27日夜21:15,正对着心爱的大银幕,崔永元开始接受采访。 少赔就行 崔永元:《手机》那件事以后,他们不是攻击我吗,说我是为炒作(《电影传奇》)。我这人还挺硬,那我就不炒,不用炒。一个节目的好坏,不是靠炒出来的。你炒得越多,观众期望值就越高,节目跟不上,观众骂得就越狠。我们现在精力都放在节目上,全身心地投入,所以现在基本上不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有没有想过,你这节目的受众在哪里? 崔永元:就是40岁以上的人。 记者:你那么有把握? 崔永元:对。 记者:40岁以上的人现在恐怕都忙着做生意。 崔永元:你说的那拨人,他们什么都不看,不看书报,不看电视,不上网。我说的是40岁以上还愿意看电视的,就做给他们看。 记者: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非常喜欢老电影,甚至会倒贴5块钱拉人看它们。但你现在做的是一个产品,要推向市场,有没有想过个人的志趣和市场之间的匹配程度?很可能,你推崇倍至的,正是市场渐渐遗忘的。 崔永元:当时是这样。我有一投资集团的朋友,有些钱,老跟我一块儿聊老电影。我说,你要那么喜欢老电影,能不能干一回不是特别考虑商业回报的事儿,就是冒风险的事儿。我说,你也别今天喝了酒跟我说大话,你想一个准数告诉我,你能承受到什么程度,是少赚、少赔、还是赔干净为止,你给我个数,我心里也有个底。他想了两天告诉我,他对商业回报没什么期待,少赔就行。我想了想,打平的可能性是有的。在商业测算上,我们谁也没认为这能挣大钱。 记者:挺有意思的:个人志趣唤醒市场记忆。就像有一茬人特别爱听罗大佑的歌,你在寻找那些热爱老电影的同道。 崔永元: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我那个朋友下了血本,支持我作这种尝试。我要尝试几个东西:一是我在过去的电影中看到中国的历史,不仅仅是有插曲,有漂亮明星什么的,不是这个概念。过去的中国电影是在说中国历史,虽然有些不是那么准确,甚至有歪曲的成分。 记者:你是指60年代以前的电影? 崔永元:80年代吧,80年代以前的都行。包括伤痕文学那些,都写了一段历史。我觉得,现在一些人之所以浅薄,就是因为不知道历史。 第二个尝试是,我认为好的产品应该有好的市场。现在好像不“戏说”就挣不了钱,没有大明星就没有高票房,我从来就不认为这是娱乐业、传媒业的发展规律。我看了一个消息,不知准不准确,说是《泰坦尼克号》到现在为止全球票房收入是55亿美元。我们知道,它是一部比较好的商业电影,但教人向善,用通俗的话说,有教育意义。像船沉的时候,那些拉琴的人还在那儿拉,我们现在说那叫敬业。它是有意义的。但它同时是商业的,你想,55亿。我们也想尝试这个。因为中国现在的娱乐市场太滥了!滥得让人无法忍受。我有点年轻小伙的情绪,照说我这年龄不应该这样,应该解甲归田了。但我就不甘心,就想试一试。 另类传奇 记者:《电影传奇》是个另类? 崔永元:《电影传奇》出来了,可能引来很多批评:说它怎样漏洞百出、怎样不完善,不符合较高的艺术水准……我现在就已经做好了接受这些批评的准备。但有一点,我们特别自豪,这是我们原创的,这个样式全世界都没有。 记者:是啊,听一些看过样片的人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包括你主持人的角色。 崔永元:我在里面肯定还是个主持人。过去我穿着便装上台主持,现在穿着戏装主持——为了把大家带到规定的情境。当你跟着我入戏的时候,我又会“跳”出来,对着镜头跟你讲背后的故事,就采用这样“跳进跳出”的方式。 记者:这个样式是怎么出来的? 崔永元:出于偶然。那是四五年前吧,有一次我们去内蒙种树,火车上,我跟于洋老师没事儿就聊老电影,他就跟我说当时拍《英雄虎胆》、《大浪淘沙》时有这样那样的镜头。我说,我们怎么都看不到呢?因为在修改中剪掉了。他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弄起来做个片子挺有意思的。那个叫编余片。在这之前,我看过一个《卓别林的秘密》,就是用编余片的方式做成的,譬如说一个动作他做了15遍,选了最好的一个奉献给观众。 记者:我们现在的电影好像也在用,在结束的时候。 崔永元:对,用一点儿。当时我就想,把余片编起来,可能挺好看。后来一问,余片都没了,八九十年代统一提银去了,因为胶片里含银。我一听,没戏了。后来,跟我的同道们聊天,说,哎,我们就不能把这余片拍出来吗?结果在调查的过程中,老电影后头的故事多着呢,非常传奇,超出你的想象,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节目叫做《电影传奇》。 记者:那是什么呢?历史知识?拍摄花絮? 崔永元:说花絮太轻了。一是这电影怎么拍出来的。你是上海来的,知道上海1959年拍的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吧。 记者:知道,仲星火。 崔永元:大家都知道它是故事片,但其实不是,它叫艺术性纪录片。所以,它当时花了多少钱?7万块钱。那时电影的平均成本是30万。它的服装费就17块5,就是借了2件民警的警服,用完给人洗洗熨熨,花了17块5。有人说,好电影是拿钱堆出来的,不对吧。《今天我休息》给你一大耳光,这就叫传奇。 最近我在做《姊姊妹妹站起来》,是讲北京挽救和改造妓女的。当时的导演是陈西禾,都管他叫学者型导演。我在《大众电影》上找到了当时他给观众的一封信,回答两个观众给他这部电影提的三个意见。他非常认真,一条一条给人解释和回答,我看了特别感动。你说我们现在的导演愿意做这种事吗? 还有,像《小兵张嘎》,那里面有一个“伟大的运动长镜头”,就是罗金保带着小嘎子从房顶上一路过去的镜头。现在随便一个导演都能拍出来,但当时没有12米摇臂,摄影师聂晶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说它伟大?我就要把这个揭示给观众看(崔随即用桌上的三个遥控器给我演示拍摄原理)。 还有一个正面跑的镜头,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在轨上拍的,因为当时没有斯坦尼康(20世纪70年代初,摄像师伽莱特·布朗发明了一种可以和摄像师的背心连在一起的便携摄像机三脚架。这个设备的配重平衡系统可以使摄像师在快速移动过程中,保持摄像机的稳定,从而拍摄出稳定的画面,这个技术被称之为“斯坦尼康”。它的出现引发了电影画面效果的革命,摄像机从此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一个镜头中从不同角度记录动作画面,而观众则可以通过连续画面更好地感觉时空),但就纳闷怎么看不见跑的人身后的轨呢?我们一问创作人员,真是让人感动:车上坐两个工作人员,每人拿一口袋土,车在走,轨露出来,那两人就赶紧地着把土倒出来,把轨盖上。这就是精神。 记者:哦,把有价值的、闪光的东西拾起来给大家看。 崔永元:对。还有一个就是更关注大的历史背景,想把这二者勾连在一起说。我觉得这样它的文化含量会高一点儿。 我挺高兴的是,中央台的几位领导看了我们的样片,评价都挺高的。我们还组织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看,他们都还是挺喜欢的,觉得有很大的信息量。 就选208部 记者: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00多部电影里选取208部,谁的眼光? 崔永元:我的眼光。选的标准大概有那么两种,一种就是好电影,像《小城之春》,无可争议的好片子;第二种,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的,就介绍给你。 记者: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 崔永元:对,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事儿简直就无法解释。他们也问我,为什么要这么选。我说,这是我做的项目,当然就这样选。如果你做,你选。我知道很多部门都想评出“100部最优秀的中国电影”,但到现在没做出来,为什么呢? 记者:没有一致的评价标准。 崔永元:对啊,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确实多种多样。现在《电影传奇》所用的是我和我所在的这个集体的评价标准。 记者:这208部电影从哪儿得到? 崔永元:参考书有《中国电影大典》,每一年生产的电影上面都有。另外我们自己有片库。 记者:你怎么评价建国以前的3000多部电影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00多部电影? 崔永元:有电影史以来,全世界有23万部电影,中国有6000多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很拿得出手,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小城之春》,现在拿到意大利还看得人家目瞪口呆呢,尤其是他们听说这是中国几十年前拍的电影。 记者:所以宽容些。 崔永元:不是宽容,就是好。可能技术上还有点差距,但影片的思想性、表现手段、包括演员的表演,跟美国电影、意大利电影都到了差不多同一个水准。 记者:你不觉得那时候的演员念台词拿腔拿调,特别难受吗? 崔永元:不是所有的片子都拿腔拿调。你看的是昆仑影业公司的那些片子,大部分是话剧演员。但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时,陶金这些人的表演已经很自然了。 我认识一外国人,以前在我们那儿(《实话实说》栏目)实习。我请他看老电影,他看完对我说,“你们以前的电影拍得真好,可现在怎么拍成那样?”把我气的,可又不知该跟他说什么。确实有些沮丧。 记者:那现在的导演中,有你看得上的吗? 崔永元:有啊,很多,陈凯歌、张艺谋、姜文、何平、冯小宁……都挺好的。但我不喜欢他们摇摆。在艺术上用不同手段去探求,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包括失误,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商业摇摆,就非常可怕了。商业的诱惑力有时候大于艺术的魅力,很容易被它俘虏。当你觉得挣钱越多越好,你就会对艺术很放纵,不会觉得艺术上的损失会给你带来心痛。 记者:那你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崔永元:我不面临。因为商业上我没有那么高的追求,我提前都跟朋友说好了,咱们做好赔钱的准备了。 记者:拍完这208部老电影,打算做什么? 崔永元:还有许多老的东西值得回忆,像戏剧、戏曲、绘画、小人书、歌曲、老手艺,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做。 电影与我 记者:你小时候最喜欢看哪部电影? 崔永元:所有老电影我都爱看,连老纪录片我都几遍几遍地看。我迷那个大银幕的东西,你看我现在坐在这儿,面对着这大屏幕,我心里特别踏实,你知道吧。 记者:小时候在哪儿看电影? 崔永元:在部队大院,看露天电影。后来去电影院,也是露天电影,旧片子3分钱(门票),新上映的5分。 记者:记不记得看过的第一部电影? 崔永元:我有印象,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广阔的地平线》,阿尔巴尼亚的。就记得有一个人从塔吊上掉下来,小时候看害怕,印象挺深。 记者:你看完一部好电影的症状是什么?我大概是半小时不能说话。 崔永元:不能自拔,久久地不能摆脱出来。我现在苦于看不到好电影,打开报纸,全是不喜欢的。 记者:因为老电影,你回访了很多当年风光、现已年迈的老演员,感受如何? 崔永元:我觉得那四个字挺合适:养育之恩。不是说他们给我们做饭、给我们穿衣服,而是他们塑造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有了一个精神的境界。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很大程度归功于这些老电影演员。 记者:你到底喜欢老电影什么? 崔永元:我说的情怀、精神,老电影里都有。我们现在创作资金充裕了,陶醉于用电脑能做出什么来,譬如弄一根羽毛。我们除了吊钢丝,还能做什么?我觉得我们有责任生产更好的精神产品,而不仅仅是商品。当然,我同意最高境界是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完美统一。但不能双赢的时候,我们应该放弃什么呢? 记者:电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崔永元:就是精神世界。它不能被玷污。你知道这点,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对电影发火要比我对电视、话剧发火更厉害。 精神洁癖 记者:看到过张越的一段文字,说你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做《实话实说》那会儿,你几乎做到精神崩溃,好多人不太理解。你能解释一下那段的心路历程么? 崔永元:不是几乎,是已经崩溃了。一个人做件事,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外界对你的要求,具体到《实话实说》,就是观众对你的要求;另一个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当时我们可能过分看重自己对自己的要求。2000年、2001年,《实话实说》在社会上口碑很好,收视率高,在台里广告份额占得也大,但是我们自己特别不满足,觉得在原地转圈。同样一个话题,我们换个角度又去说。有一阵我精神恍惚,坐着的嘉宾,我都觉得好像来过,采访过,那种感觉挺可怕,就好像是演戏了。也许观众可以原谅我们,但我们已经无法自我原谅。转圈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还在下滑,所以我当时觉得承受不了了。 《实话实说》,还有《电影传奇》,我都把它们当成个“事儿”来做,而不是当做一个“活儿”来做的。如果当做个“活儿”,就用它来养家糊口就行了,可能心态就会好。 记者:《手机》事件其实引出来一个很好的命题,就是我们今天怎样来做文艺批评。听说有些评论家打电话给你,说你那篇长文里还应该引经据典,譬如马克思怎么说,鲁迅怎么说。 崔永元:我当时就问他,你怎么不写呢。他说,我们不方便。你就干这行的,你却说不方便。现在的文艺批评,要么隔靴搔痒,要不就是肉麻的吹捧,这两样一样可怕。我对电视的批评比电影要早,两年前我在现代文学馆做过一个演讲,专门讲电视的庸俗化,那是花了一年半时间做的一个研究。 记者:电视庸俗化,我记得你在《实话实说》里也谈过。 崔永元:对,但说完没什么用,同行之间也没人理会。因为大家都面临收视率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谁来跟你扯这个庸俗不庸俗的问题。高雅不挣钱,就得庸俗。北京一个专门搞文艺评论的记者,就在他们报纸上发了一篇稿子,说“庸俗怎么了,老百姓就喜欢庸俗”。当时我就真想搧自己两嘴巴,我还说什么,我跟谁说啊﹖ 记者:确实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在支撑人们的信念。 崔永元:凭什么说老百姓喜欢庸俗?谁有资格说这个话。《大河之舞》在北京连演7场,全满;上海演《猫》,70多场吧;还有《图兰朵》、《悲惨世界》,哪儿庸俗了?再说,即便老百姓真的喜欢庸俗,那是件好事儿吗?所有媒介的从业人员都要反省,都要反思,都要承担责任。如果老百姓真喜欢庸俗,我们就给提供庸俗,这行吗?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精神境界,完全是由艺术家们构成的。所以,他们负有责任。如果你是艺术家,就不允许你像商人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能挣多少挣多少。 你看我什么时候跟商人较过劲?即便我做了节目,有了一点话语权,我也从来没跟商人较过劲。跟商人说你少挣点钱,那是你有病。但我们跟作家、艺术家,跟构筑社会精神世界的一些人,跟承担社会良心、道德责任的一些人,就有权利和义务来说这样的话。 记者:你有使命感。 崔永元:不是我有,我觉得做这行的都应该有。 记者:我觉得,你批评的范围好像得扩大,你刚才已经说到小说家了。 崔永元:唔。这是个原则问题,这样来要求作家、艺术家,不为过。 记者:你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吗? 崔永元:我要是作家、艺术家,我就这样要求自己。你看我从1996年开始在中央台做主持人,到今天为止,没有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我敢对媒体这么说。有人让我去做一广告,给我500万,还有一企业让我做形象代言人,也给500万,加起来就1000万。我们家族祖祖辈辈都没挣过这么多钱。 如果我们来算账的话,你说我损失了多少?我觉得做这个行当,我已经向作家、艺术家,向那些美好的东西靠近了,所以这时候我一定要拒绝商业的诱惑。 记者:是什么,让大伙儿都往那方向走? 崔永元:我想不通。我觉得没什么能让他们变成那样。我们知道,贝多芬、梵高这些人都是穷困潦倒的。当你心灵里充满艺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空虚,不会觉得饭吃得不好很难受。艺术占据了你的心灵,是这种感觉,知道吧。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当你去听一场好的音乐会、看一张好画、读一遍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那种愉悦,不是拥有一件名牌衣服或者一双名牌皮鞋可以代替的。我要能写出《荷塘月色》来,你就是拿两幢别墅来我都不换。它们不等价,没法比。 记者:我懂。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跟你一样,这有点儿像揪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电影传奇》投资多少? 崔永元:投资非常高,现在已经超过800万(元)了吧。 记者:如果有人出8000万,让你顺着他的思路改,迎合市场…… 崔永元:8个亿都没用,我绝对不会妥协的。最近我不是把老唱片拿出来了,他们跟我商量,用什么题目,我说12年前我就想好了,就“宁死不屈”;问用什么封面,我说就我手拿爆破筒,宁可同归于尽,也不妥协。 记者:你靠什么坚守?不让那种欲望膨胀? 崔永元:就靠我看这样的电影长大,看这样的书长大,脑子里有我敬仰的这些人。他们能这样活一辈子,我也能这样活一辈子。 记者:你是不是一个精神上有点儿洁癖的人? 崔永元:可能,有点儿。 记者:每回看见一个“坏”书名、一部“坏”电影,哪怕一个姿势或造型,你是不是都特愤怒? 崔永元:是这样,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找找自己的原因:你不够宽容,你没与时俱进。但有时实在让人受不了。你像我每天回家坐电梯,那电梯师傅跟我挺好,我们老聊天。他开着半导体,我一听里面唱的那流行歌,我就真想从电梯里出去。 记者:唱什么呢? 崔永元:唱上厕所什么的,还骂人。那叫什么歌啊。 记者:那叫HIP-HOP,流行着呢。 崔永元:说唱也能好好说,陕北说书我听过,好听极了。 记者:我明白了,你是不是特反感低级趣味? 崔永元:对,就是反感低级趣味。我现在这么想,我可以低级趣味,你可以低级趣味,艺术家也可以低级趣味,但你的作品不能低级趣味,因为要对社会负责。我可以抽烟,但我不能告诉大家抽烟好,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记者:你的这种精神洁癖这些年给你带来什么?估计是受伤挺多。 崔永元:伤害非常大,我得了重度抑郁症住医院去了。住了2个月,吃了一年半的药,现在每个月还要去复查。 记者:医生怎么说? 崔永元:他希望我卸掉这个责任。他说,我不跟你谈社会责任感,就谈身体。但我走在街上,坐在办公桌前,坐在电视机前,我一下又回来了。 记者:像你这样的人,你们单位多吗? 崔永元:我觉着还是挺多的。可能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更多的人选择洁身自好,不像我,扛着爆破筒冲出来。当我抨击那些恶俗的东西时,台里的人大多数都从道义上表示支持,还跟我说“注意身体,别那么焦躁”。 记者:你怎么描述你自己? 崔永元:我缺点特别多,像抽烟哪,说话随便啊…… 记者:别净拣轻的说。 崔永元:有时候还傲慢,然后半瓶子醋,学问修养不够,这都是很严重的缺点。但我的优点也特别明显,像坚守。我觉得现在坚守的人太少了,大部分人都选择放弃。 记者:还有随波逐流。 崔永元:对。放弃可能一分钟就能决定,但坚守得一辈子。我坚守的底线在不断下降:以前我说艺术家首先要做人,然后才有好作品;现在我说艺术家可以不好好做人,但你的作品得好好做人。我已经放弃一些了。 记者:如果你坚守的价值判断异于大流,会不会觉得对自己不公平? 崔永元:我只是觉得对社会不公平,对孩子不公平。美国不是都不允许珍尼·杰克逊在公共电视网上露乳,很简单,有五分之一的观众是2岁-11岁的孩子。她最近还有低俗的表演,家长就带着孩子退场。这是人类坚守的底线,而不是老崔自个儿坚守的底线。 (《电影传奇》每周六央视一套:7:15,16:00,新闻频道:14:10,周日03:10央视四套:15:15)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